2023年的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分别以“信步西东”“西行画录”“长春园迹”“旅欧画录”等为主题,开设了多场别开生面的水彩和铅笔画展,画展的主人公并非是某位声名显赫的画家,而是一位近年来才在专业领域之外为人知晓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叫童寯。2023年正值童寯逝世40周年、出版代表作《东南园墅》60周年;北京、上海、南京,正是他求学深造、事业起步、传道授业的三座重要城市,在这里,他结交了梁思成、赵深、陈植、杨廷宝、刘敦桢等一批重要的建筑师,和他们一起营造了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建筑。
北京
2018年,一本名为《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的传记,意外成为了出版界的“黑马”。这本叙事上近乎白描、语言上极为简练的“小传”,记叙了作为“中国建筑四杰”之一的童寯人生最后20年的光景。在该书第六章《为费慰梅追记梁思成》中,身为作者和童寯孙媳“双重身份”的张琴,讲述了童寯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三重交集:一是他们结识于北京,早期是清华学堂的同学;二是他们一起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既是同窗又是舍友;三是他们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共事,童寯还曾接替梁思成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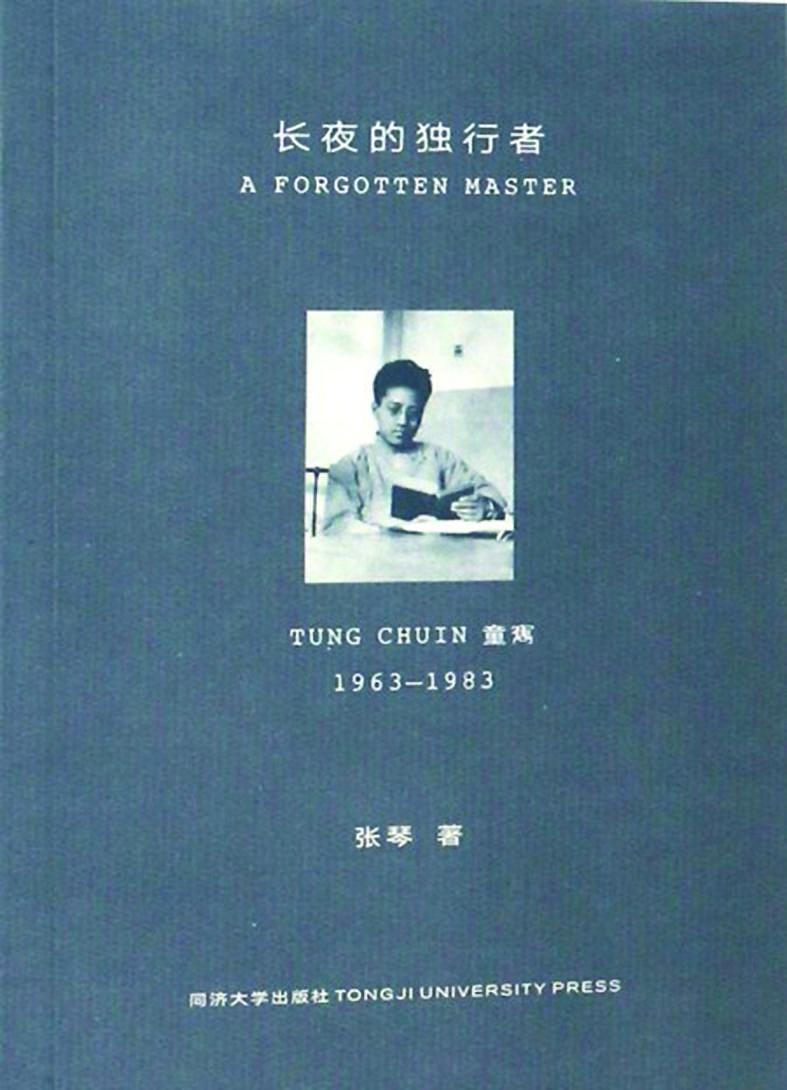
《长夜的独行者》 张琴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然而,童寯与梁思成的交往,却似乎有些“高开低走”。在人生的上半场,他们是最为亲密的同学和同事,书中讲述了“童寯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于梁思成一如既往的喜爱”,也引用了梁思成对童寯的激赏,称童寯执教东北大学是“国破家亡、弦歌中辍之时的一线曙光”。而在共同抵御过苦难岁月的侵蚀之后,童寯对梁思成的态度却有些转冷。《长夜的独行者》以影印的形式刊载了一封1950年梁思成写给童寯的书信,在信中,梁思成自称“弟思成”,称童寯为“老童”,已足见关系之亲密;短短一页的书信正文里,邀请童寯北上清华任教的梁思成多次写道:“我企盼你早早的(地)北来”,“我恳求你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他们(学生)都在切盼”,“我恳切的(地)求你来为母校养育后辈”,“恳切拜上”,言辞至真至诚可见一斑。不过,事情的后续似乎有些令人失望,童寯并未应邀北上,而对于梁思成的来信,童寯如何回复或者是否回复,也已不得而知,但用作者张琴的话来说,那就是“自1950年代起,这两个昔日的同窗好友联系似乎不那么频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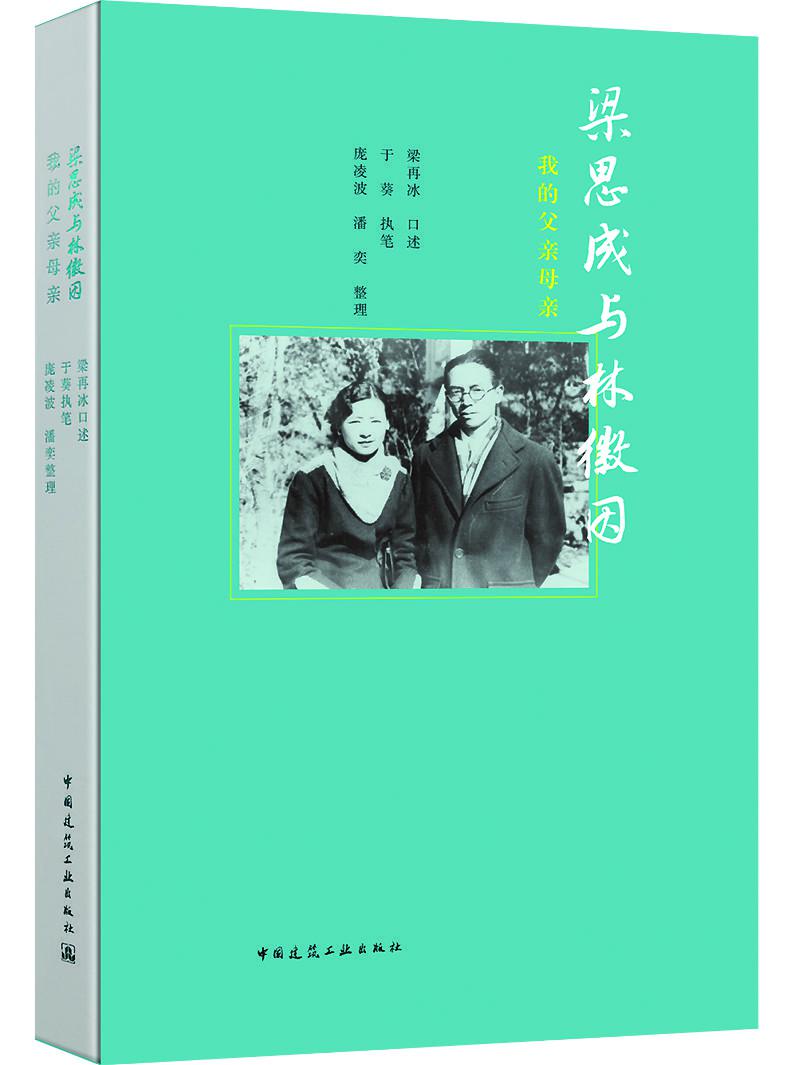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与母亲》 梁再冰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所谓“联系不那么频繁”,意指的当然不是交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是对于时事和社会的不同认知,导致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差异,但即便如此,童寯和梁思成的英雄相惜、童家和梁家后人的世代交好,永远都无法轻描。1994年,汉学家费慰梅撰写的《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美国出版,并于数年后译介到国内,正是这本书,把梁林夫妇从漫无天际的“花边”和“八卦”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了他们作为“建筑学家”的本来面目。而此书的顺利面世,也得益于童寯的贡献,“从1980年起,童寯与费慰梅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以帮助她出版梁思成的遗作,并为她撰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传记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童寯)手术后半年多即去世,在这期间他们(童寯和费慰梅)一直在为出版梁思成的书而频繁沟通”。
此外,梁思成的继配林洙在回忆童寯1982年的清华行时也讲道:“我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好朋友,我也很敬重他。”在梁思成之女梁再冰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与母亲》中,每次提及童寯,都尊称“童伯伯”“童寯伯伯”,甚至还附带一串长长的定语“爹爹的好友、他极为欣赏的童寯伯伯”;在该书后记中,梁再冰再次强调童寯是“父母最好的朋友”。而张琴所著的另外一本著作《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的后记中,也留下了童家后人对梁家后人的诚挚谢意:“感谢梁思成等先哲和先贤的亲友,他们使此书的写作充满惊喜和温暖。”
上海
在《长夜的独行者》中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童寯曾经为自己刻过一枚私章,上面写着“童寯建筑师”;无独有偶,《梁思成与林徽因》中也记录了另一个细节:纵使林徽因有着各种耀眼的光环,但她的墓碑上也只是简单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六个字。无论在炮火连天还是和平安定的岁月,“建筑师”都是他们最为珍视的身份。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 张琴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3年元旦,同为宾大建筑系留学生的赵深、陈植和童寯,在上海成立华盖建筑事务所。关于“华盖”的理论观点,蒋春倩所著的《华盖建筑事务所1931-1952》引用了陈植的原话:“三人相约摒弃大屋顶”,也正因为此,华盖建筑事务所被建筑界誉为“求新派”。至于“华盖”的命名,《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中也有说明:“一寓意为中国建筑师在中国盖楼;二愿景为在中国顶尖,盖为‘超出、胜出’之意。”除此之外,童寯还有另外一番解释,他认为:“紫禁城内的朝政三大殿,华盖殿是最中心的宫殿。从星象角度来看,华盖意味着高于凡人的成就和才华;在命理来看,系心情恬淡,资质聪颖,有文学才能和艺术才华,但又不免有些孤僻。”
童寯对“华盖”的释义,驰骋于建筑学、星象学、命理学等多个领域,足见其知识的广博。事实上,同时代的中国建筑师们都不只是偏于一域的人才,除了林徽因早已诗名远扬之外,根据《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介绍,梁思成和陈植在求学期间都担任过小号手,陈植还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岱峻所著的《发现李庄》中记录了莫宗江“写得一手好字”“他的画很有表现力和艺术感”;《长夜的独行者》也写道,“对于西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几乎贯穿童寯一生”。然而,即便贯通中西、多才多艺,也即便面临过多种多样的人生抉择,他们都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建筑事业的绝对热爱,“为中华盖楼”成为他们热忱终身的无悔追求。
经历百年风雨,如今的上海仍然留下了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现宝龙大酒楼)等诸多由华盖建筑师呕心沥血设计的精品力作,在不少沪上名人的书中,这些伟大建筑师的故事,也在时代和历史的浪涛中得以浮现。陈丹燕的《外滩:影像与传奇》就记叙了记者杨俊和时年已经95岁高龄的陈植,因为1950年代保护汇丰银行壁画的往事而相识的经历。初次见面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在这位“穿着蓝白条子病号服的老人”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风华正茂的模样,“握紧助听器”的陈植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不时用手拍打自己的头”,无奈地声称“过去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得了”。即便是后来已经努力回忆起了那段保护“世纪壁画”的往事,陈植仍然如同几十年前一样淡泊名利,他逃避了电视台的采访,只是留下了一句:“保护壁画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决定,我已经老了,就不再抢镜头了。”在《我要唱到永远》中,曹可凡也借由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居住的“锦园”,追忆起了锦园当年的建筑师赵深,曹可凡坦言,“近日读到《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得以一窥赵深先生作为一代建筑大师,对中国现代建筑事业所作的贡献。”事实确实如此,若非“建筑可阅读”浪潮的兴起以及有识之士们的挖掘,诸如赵深这样的建筑师以及他们作出的卓越贡献,很可能已经永远遮蔽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南京
1952年,华盖建筑事务所解散,陈植和赵深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只有童寯一人去往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从事建筑教学工作。虽然没有明确的著述出处,但是从童寯的毕生好友杨廷宝、刘敦桢当年都在南京工学院执教,或许可以窥知童寯离沪赴宁的主要原因。
《长夜的独行者》用较大篇幅讲述了童寯晚年与杨廷宝之间的深情厚谊,两位建筑大师的友谊跨越半个多世纪,无论是经历特殊年代的捶打还是声色名利的考验,都始终未曾变质,用作者张琴的话来说,那就是“两位老人的命运似是紧相耦合”,童寯也曾说:“经过解放到现在,我们几乎每天见面。”

《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 黎志涛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982年,杨廷宝因脑溢血已快进入弥留之际,但他仍然惦记着童寯,甚至还想着要与老朋友转院住到一起;而童寯也是手术放疗一有间隙,就催着儿子用三轮车拉着他去看杨廷宝,两位老人只要见面,就总是“兴奋异常”“长久紧紧握手”。黎志涛所著的《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以寻访的形式介绍了南京城里杨廷宝设计的现存建筑及其前世今生。值得一提的是,杨廷宝与童寯虽然至交,但书中言及童寯的文字却少之又少,仅有几处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原因想必是晚年的童寯已经完全绝缘于建筑设计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因此我们在杨廷宝聚光灯下的“建筑活动”中很难寻觅到童寯的身影,但倘若有一部“二老私语录”,那童寯必是其中的重要存在。
童寯最初走入大众视野,还是因为2017年王澍的建筑随笔集《造房子》的“走红”。这位一度被视为乖张另类的世界建筑学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获奖建筑师,却在书中用极为谦卑的言语,不厌其烦地引用童寯的造园理念,感佩童寯的为人处世,他认为“童寯先生是真有文人气质和意趣的”,“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2018年,由童寯之孙童明重译的《东南园墅》出版,在前言中,作为《东南园墅》最早一批读者的王澍,再次坦陈“《东南园墅》对我的建筑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并且回顾了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与童明的交往旧事。在童寯的三代亲属中,儿辈有电子科学家童诗白和“九叶派”诗人郑敏夫妇、物理学家童林夙、航天专家童林弼,孙辈也有从事电力、通讯、艺术等领域研究的童琅、童文、童蔚等人,但继承童寯建筑设计衣钵的就只有孙子童明了。2021年,童明选择离开执教22年的同济大学,回到祖父童寯曾经任教30余年的东南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这或许可以被视作一种精神和力量的接续,正如《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里所记叙的陈植在听闻别人祝贺他的外孙和童明也选择攻读建筑专业时,所说的那句话:“总得一代胜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那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