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1921—1995),世界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学家和哲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心理学系。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1951年在瑞士联邦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51—1953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1954—19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第二套洛克讲座讲演,又任逻辑及数理哲学高级教职。1961—1967 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7年后任美国洛克斐勒大学教授,主持逻辑研究室工作。1985年兼任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兼任中国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数学到哲学》,[美]王浩著,高坤、邢滔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王浩无疑是一位科学巨匠,他在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贡献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但从学生时代起,王浩就立志要研究哲学问题。据他在一次访谈中自己讲,高考时他原本想报考西南联大哲学系,只是因为父亲反对,才改了数学系。虽然身在数学系,但并不妨碍他选修各种哲学系课程(特别是金岳霖、王宪钧和沈有鼎等人开设的逻辑学课程),以及进行广泛的哲学阅读。比如,在《从数学到哲学》(以下简称《数哲》)中,王浩回忆说,1940年他还是大一新生时,就已经开始对着罗素《数学原理》中的哲学段落苦思冥想(137页);而据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好友何兆武说,大一刚入学不久,他就在图书馆里碰见王浩读一本大书——德文本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何兆武口述:《上学记》增订版,文靖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224页)。
由此可见,王浩的哲学兴趣发端很早。这种兴趣贯穿了他此后的人生,本科毕业后,王浩即进入清华研究院哲学部学习,之后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跟随分析哲学大师蒯因学习,后来又辗转任教于牛津、哈佛、洛克菲勒等大学,从事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相比之下,他的许多科学工作反倒具有玩票性质,比如,他在五十年代之所以去研究计算机,只是因为当时考虑要回来建设新中国(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未能成行),需要具备一些有实际用途的知识,而他已有的哲学和逻辑知识似乎于工业化建设无甚用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此而割裂王浩的科学工作和哲学兴趣,则又大谬不然。实际上,王浩热烈推崇的是以爱因斯坦、哥德尔等为代表的哲学-科学家传统,他的哲学思考和科学工作互为促进,是一体两面的。这也反映在了《数哲》一书的书名中。对于王浩来说,科学,尤其是包括数理逻辑在内的数学,对哲学是至关重要的。但数学为什么对哲学重要,它与哲学之间具有怎样特殊的关系,还需要多说几句。

王浩(1921-1995)
为什么是从数学到哲学?
乍一看,数学与哲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而从现行的学科划分来看,情况也确是如此。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柏拉图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斯宾诺莎模仿《几何原本》中公理—定义—定理—证明—推论的体例写作他的《伦理学》;康德从追问数学知识如何可能开始他的哥白尼革命;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如弗雷格、罗素、胡塞尔等,无不是学数学出身,且将逻辑-数学知识作为核心反思对象。此清单可以继续延长: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蒯因、普特南、克里普克等,数学在所有这些人的哲学思考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些光辉的例证,足以证明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但要解释为什么如此,则还需要诉诸数学本身的哲学性质。
在这方面,柏拉图的一些想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柏拉图有一个四线段的著名比喻,把世界划分成四个领域,即影像、知觉对象、数学对象和理念或相,影像和知觉对象构成可感界,数学对象和相构成可知界,前者是有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后者则是绝对的、不变的实在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花了不少笔墨谈教育,在他看来,教育就是灵魂转向的艺术,让灵魂之眼从可感世界转向可知世界,从信念、意见转向真正的知识。而在这样的转向中,数学学习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因为数学对象本身虽然还不是相,但和相一样不在时空之中,超脱于一切生灭变化,介于可感物与相之间,数学知识作为推理性知识,也对意见与关于相的理性知识起到连接作用。因此,柏拉图认为,人们在进入哲学学习之前,应该先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学习十年数学,这样可以帮助他们的灵魂实现从可感界到可知界的转向。
柏拉图的上述思想,实际已初步揭示出了数学的两点特异性,即本体论和知识论上的特异性。
从本体论角度讲,数学对象如自然数、集合和函数等,既不具有时空属性,也不接受因果作用,与普通可感对象有明显差别。比如,你不能说0在北京还是上海,它何时何地产生(注意区分人关于0的概念和0本身),你也不能设想去踢它一脚。而且你也很难说0不存在,或仅仅是像孙悟空那样的想象物,因为我们似乎确有关于0的客观知识。因此,0似乎是一个抽象实体,它不在时空之中,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着。一般地,所有数学对象都显示为这样的抽象实体,这就是数学在本体论上的特异性。
从知识论角度看,数学同样显示出惊人的特异性,而且这种特异性具有更多面向。首先,数学知识似乎不依赖于对世界的经验观察,而且似乎是绝对确定无疑的,比如,假设有人在数羊,他发现7只羊加5只羊数出来不是12只羊,那么他一般不会认为7+5=12是错的,而会认为一定是自己数错了。也就是说,数学命题不接受经验观察的证伪。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称数学是先天知识,而且康德还认为数学知识还是综合的,他的哲学的起点,就在于回答这种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数学知识的另一个特异性是,相比于其他知识,数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严格性、清晰性和精确性,以严格的演绎推理为基本扩充手段,这使得数学成为知识的典范,也正是因此,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者,将数学作为哲学效仿的对象。最后,数学知识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普遍的可应用性,数学在所有科学分支中都有广泛应用,诚如伽利略所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就的。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数学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两方面都异常独特,这就决定了数学在哲学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以致许多哲学家(比如哥德尔)会把数学看作形而上学的试炼场,或者反物理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当代哲学中,数学哲学已被普遍承认为哲学的核心部门。因此,王浩的书名毫无可怪之处。《数哲》一书所主要关注的,正是数学(包括逻辑)的哲学性质。

王浩与哥德尔
实质事实主义:超越分析哲学
不过,虽然数学哲学问题是《数哲》一书的核心议题,它们却远非《数哲》的全部。在该书中,王浩还力图阐明一种更一般的哲学立场,即他所谓的“实质事实主义”。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元哲学或哲学方法论立场,因为它关乎我们应该如何做哲学,反映了王浩对哲学的总体理解,而书中具体的数学哲学讨论,则显示为对该方法论立场的一次践行。
实质事实主义的基本想法是,已有知识对哲学享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哲学家们做哲学时,应当充分尊重我们的已有知识。因为,据王浩讲,我们对我们知道什么,比对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知道得更多;我们对我们相信什么,比对我们这些信念的终极理由为何,知道得更清楚。当然,我们的已有知识十分庞杂,其中有些可能具有更基本的、概念上的重要性,有一些则仅具有技术性价值,对于实质事实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基本知识或概念性知识,而不是技术性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尊重的是我们已有知识的实质事实。这里的界线可能无法严格地给出,但王浩强调,清晰表述该区分并不是必要的,在实践中,误将科学中特殊的技术性细节当作哲学材料的风险很低,对于特定的陈述,我们一般能看出它们是否为真,是否重要,是否具有超出纯技术以外的价值。
从实质事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王浩倾向于反对以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等为代表的第一哲学和基础主义传统。(但要注意,王浩对康德和胡塞尔的具体工作,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包含许多肯定的成分。)按照此传统,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认识论批判,澄清知识可以可能,并确定某种第一原理,为普通科学知识奠定更坚实、更可靠的基础。在王浩看来,至少目前完全看不到这条道路的希望,没有充分证据能让我们相信,“哲学作为一门超级科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可行的”(第9页)。我们不能期望超越现有知识,跳到更高的层次上思考,达到某种包含现有知识为其特例的更普遍的真理。
另一方面,王浩对二十世纪流行的各种分析哲学派别,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和蒯因式的经验主义,也持强烈甚至更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哲学都没有严肃、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过分强调空洞的人造结构,用所谓可证实性标准衡量一切知识,将知识粗暴地区分为分析的和经验的,并试图在各种层面(包括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和语言学的)上对知识进行或物理主义或现象主义的还原,在进行这种还原时,他们采取了异常狭隘的经验概念。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比思想本身更清晰,同时又能揭示思想的最基本特征,但他们过分耽溺于琐碎的语言分析,遗忘了数学、物理学等精确科学所提供的广阔的知识疆域,让哲学走向一种新经院主义。对语言的痴迷,使他们远不能充分利用人类的已有知识。至于蒯因,他以整体论的方式把所有知识塞进一个无缝的信念之网,取消知识间一切质的差别,尤其将数学吸纳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也没有公正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王浩指出,蒯因乐于抹杀差异,喜欢进行一些笼统的、一概而论的比较,而他则更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念,认为相比于表面的相似性,更有意义的是差别。那些以同质地重构人类的知识为目标的哲学规划,注定都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它们预设了哲学家对知识的一种特权。
王浩的实质事实主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界盛行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有明显相似性。自然主义明确主张摒弃第一哲学,认为正是在科学中,实在被辨认和描述。科学方法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好方法。哲学家们应当信任科学,在现代科学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特别地,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应该自然化,在科学理论内部探讨我们的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在经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探讨认识论问题,等等。而王浩也明确说,我们接受以下为一个原始事实:“在科学提供了普遍接受的答案的那些方面,科学所绘就的世界图景就整体轮廓而言是真实的。”(456页)因此,毫无疑问,在尊重科学知识这一点上,实质事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一致的。
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王浩对自然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蒯因却多有批评。实际上,王浩肯定了蒯因自然主义的事实主义成分,但认为蒯因言行不一,未能公正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抛开具体的数学哲学观点和争论,一般地比较王浩的实质事实主义和流行的自然主义,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一个根本的差异在于,王浩从事实主义引申出的是知识学(epistemography)研究纲领,而自然主义者得出的却是哲学自然化纲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以及许多核心哲学概念如意向性、真、先天性、分析性和必然性等概念的自然化)。王浩认为,认真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就会发现,流行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过于抽象和简化、脱离实际知识太远,我们应当用一种描述、分析具体知识的知识学替代它,而避免落入各种还原主义的陷阱。王浩的这种知识学研究,强调要严肃对待已有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如自然数、集合和机械程序等,并在其自身层面上研究它们。这一理念引导他做出了独具特色的数学哲学研究。
数学知识学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自己时代的已有知识做百科全书式的考察。王浩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将自己的知识学考察限制在几个他比较熟悉的精确科学的领域,即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实际都可算作广义的数学)。具体说来,王浩在《数哲》中主要关注如下一些基本概念:自然数、连续统、集合、逻辑真、逻辑常项、证明、形式系统、一致性、机械程序、人工智能,等等。在对这些概念进行知识学刻画时,王浩既广泛引用了历史上人们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又紧密结合了数理逻辑中与它们有关的大量技术性结果,为我们呈现出一幅重峦叠嶂、江河万里的概念画卷。但由于知识学研究的本性(反对抽象简化),以及此处的篇幅限制,我们在这里无法对王浩的这些刻画逐一进行概括,仅略谈以下两点,让读者稍稍领略王浩知识学研究的风采。
(1)集合的概念
王浩在《数哲》中单辟一章讨论了集合的概念,它是王浩知识学研究的一个精华部分,当代著名数学哲学家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就曾评论说,该章应该被所有寻求对此问题之成熟理解的人当作第一读本(参见邢滔滔《逻辑之旅》译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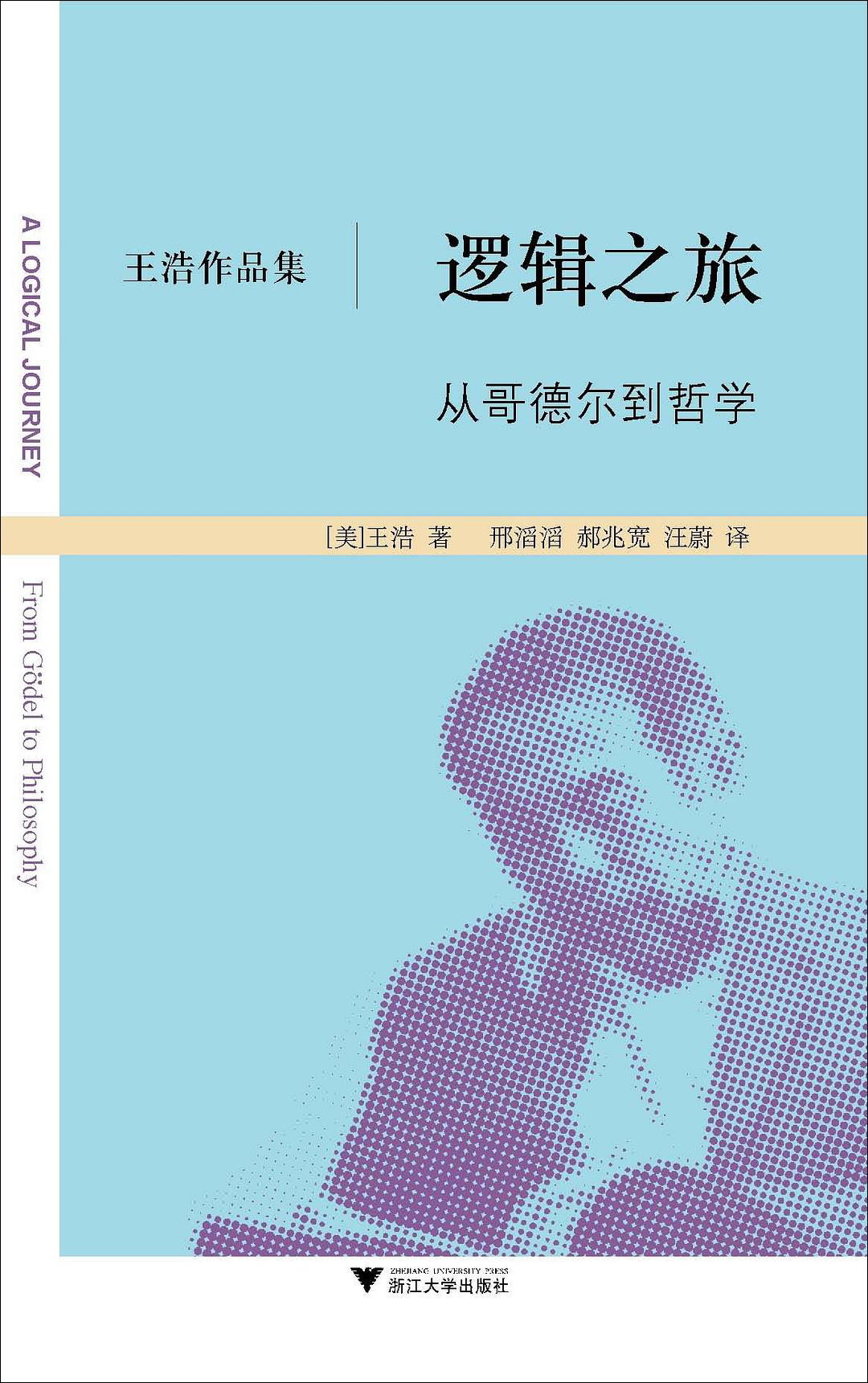
王浩著《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
集合的概念是整个现代数学的基础,现代数学的所有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在集合论的公理框架内得到解释。但我们对集合的直观概念,一开始并不是清楚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回顾弗雷格和康托有关集合概念的论述,王浩指出,他们分别代表着关于集合的两种不同的直观概念,一个是关于集合的二分式概念,一个是关于集合的迭代概念。前者认为集合是通过将所有事物的总体划分为两个范畴得到的,其标志是接受不加限制的概括原则,即每个属性都能确定一个集合(由满足该属性的所有对象组成);后者则对集合采取一种“生成式”的理解,认为集合是从一些给定的对象(也可以是空无)出发,通过迭次运用“……的集合”这个运算得到的东西。
弗雷格对集合持二分式理解,这是清楚的,因为他将集合等同于概念的外延,而康托是否已经达到了关于集合的迭代概念,则不是那么清楚。但王浩仔细分析了康托的著作,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康托对集合的生成式定义与集合迭代概念极其相符,并且他进而指出,这部分解释了二人对悖论截然不同的反应:对弗雷格而言,悖论意味着集合论的崩溃或破产,而康托则认为,悖论只是表示我们还未正确理解集合的概念。除了康托,王浩还讨论了策梅洛、冯·诺依曼和米利曼诺夫等人关于集合的一些论述,指出他们与康托具有基本相同的集合概念,即集合迭代概念。王浩还细致地说明了,从这样的直观概念出发,我们如何可以核证通行的集合论公理,甚至更多的新公理,而这些新公理或可有助于判定一些独立性问题,如连续统问题。
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一点是,王浩区分了关于集合论的一组渐强的观点:存在一种直觉迫使我们接受现有公理;这种直觉能产生更多公理;所产生的新公理有收敛趋势;它们能产生一个唯一的模型并判定连续统假设;集合客观存在并且我们能感知它们(248页)。
些细致的区分既展示了王浩数学知识学研究的精微奥妙,也与数学哲学中后来的一些著名思想遥相应和。比如,麦蒂(Penelope Maddy)有关数学自主性的论题(该论题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即在于对哥德尔的如下解读:哥德尔有关连续统问题有意义性的观点不依赖关于集合存在的本体论观点)和她对数学深刻性(mathematical depth)的强调,都可以说与王浩的这些知识学思想高度相似。
而令人奇怪的是,后来的那些数学哲学家似乎并没有在这方面给王浩任何credit,这或许是因为,王浩的知识学研究在精神上继承的是传统的数学基础研究,具有浓厚的老派风格,比如,他喜欢按论域大小和方法限度区分各种基础观点,并给出了一个五支分法——严格有穷主义、有穷主义、直觉主义、直谓主义、柏拉图主义——而基本未参与七十年代以来数学哲学中围绕抽象对象和贝纳塞拉夫问题的主流争论。
(2)心灵、大脑与机器
在今天的哲学中讨论心灵与机器,一个著名的主题是现象意识问题,其背后基本的直觉是,无论机器在能力或功能上多么出众,仍然很难设想,它如何可能具有现象意识,即那种私人的、主观的、第一人称性的感受质,如颜色的感受、疼痛的感受等。但王浩对心灵与机器的思考,基本集中于它们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别。这既是王浩那个时代的一般状况,也与王浩本人的技术性工作有关。不过,相比于许多人热衷于从数理逻辑的结果(如不完全性和不可判定性结果)论证机器绝无可能做什么,王浩同时强调了更具建设性的一面,即如何让计算机做更多的事,从而从他那个时代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出了展望。
王浩对哲学的基本设想中,人心了解客观实在的能力的范围与本性问题,是知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数哲》中,他用了整章篇幅来谈论此话题。他主要关注计算机的影响,因此人与机器的问题收缩为心灵与计算机的问题,在此范围内,他在《数哲》中思考了人工智能与理论心理学的关系,比较了大脑与计算机,同时也尝试从关于理想化计算机的数理逻辑结果得到一些大的哲学推论。但由于前面已提到的理由,下面我仅摘出一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段落,就之稍谈几句感想。
王浩在《数哲》中写道:
在心理学层面,人一般通过例子来学习,而计算机则只能按完整、详尽的指令行事。我们非常希望能引入一些方法,使得计算机能像儿童一样从几个例子中概括出覆盖广泛相似情形的特征。目前还难以看出,我们如何能通过巧妙的编程实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提取数据(经验),还是提取借以从数据得到那种普遍化的机制(学习过程),抑或是用计算机术语表达所得到的那种普遍化,都是很困难的。(360页)
这段议论反映了王浩的一个核心信念:人心的本质能力在于习得和思索新概念的能力。王浩认为,该能力是哲学一直试图破解,但屡试屡挫的一个奥秘,而许多哲学争执,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后果,即一旦破解了这个奥秘,许多争执就会消失。
趣的是,哲学自然主义在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呼应了王浩的这些观点。哲学自然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即在于概念表征关系的自然化,而最近三四十年来,自然主义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这些努力与认知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密切相关,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一条新生血脉。特别地,人脑中的数学概念是否是表征性的,是否具有更特别的认知性质和功能,是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这方面尤其可以参考莱考夫《数学从哪里来》和叶峰《无我的物理主义研究》等著作。
另一方面,具体到王浩谈到的计算机的学习能力问题,最近十几年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可以看作对此段文字的一个回响。虽然与儿童从少量例子习得高效概念的能力相比还远远弗如,深度学习技术却确实使计算机具有了从例子进行学习的能力。此外,很明显的一点是,深度学习并不是从例子去概括一般特征,而是基于复杂的统计计算做出正确预测,这反过来让我们反思人脑的工作机制,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人脑习得概念也主要不是从例子概括特征的过程,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神经元网络计算。
知识与生活
王浩留给我们的主要哲学遗产是知识哲学方面的,但应该注意的是,他也始终关切人生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据何兆武回忆,硕士毕业答辩时,金岳霖先生(但据王浩本人在《从昆明到纽约》一文中的回忆,发问者是沈有鼎先生)曾问王浩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的回答是:“我想解决人生问题。”(《上学记》增订版,228页)而在《数哲》中,王浩引人注目地用了一章(《关于知识与生活的札记》)的篇幅,专门讨论知识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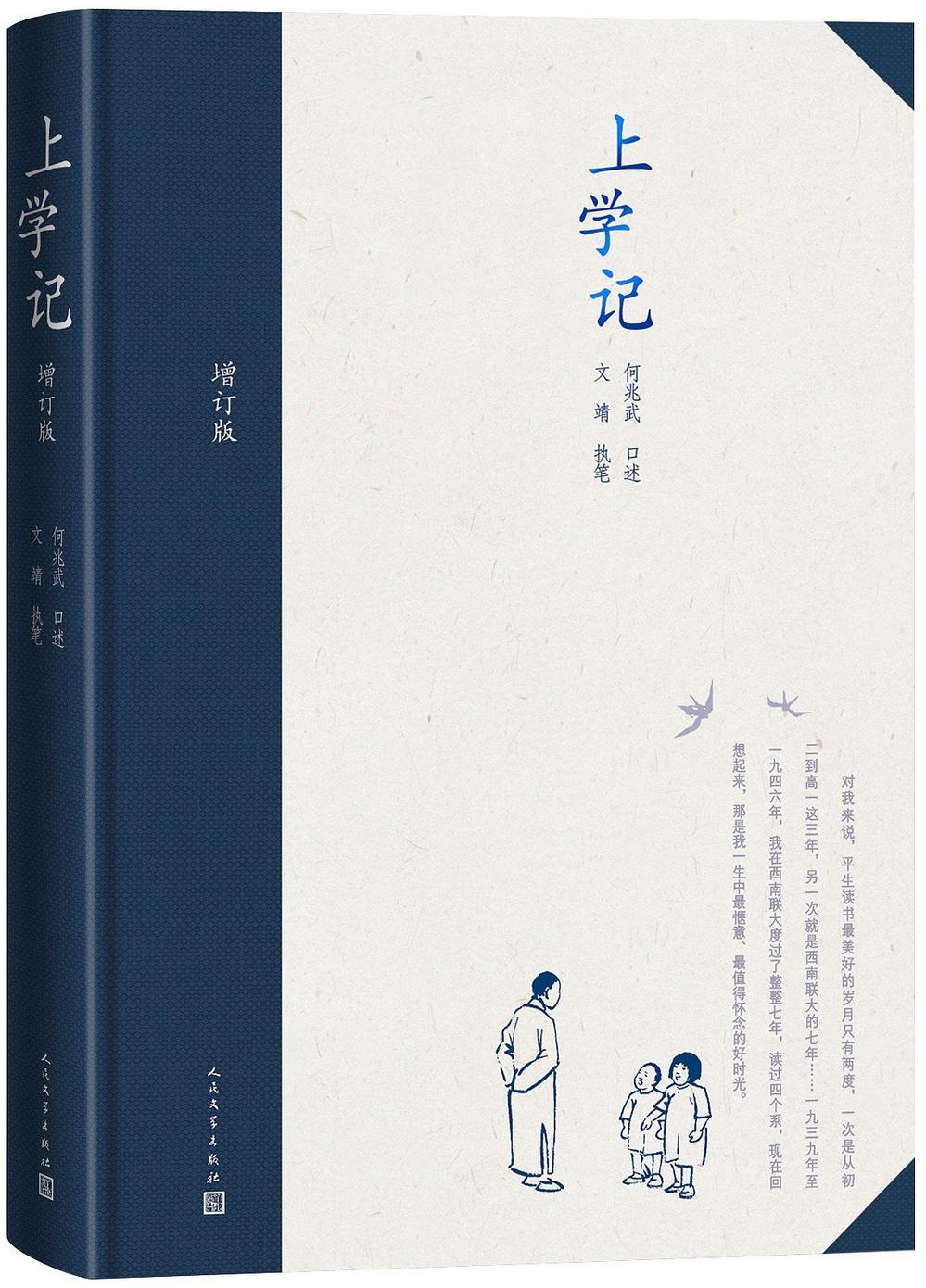
何兆武的《上学记》
如果仅就个人品味和偏好而言,对王浩来说,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沉思的生活,或追求知识、追求对世界的理解的生活。何兆武也说,有一次他和王浩讨论幸福问题,王浩最终同意了如下说法:幸福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同前,226页)。但生长于那个家国乱离、社会动荡的年代,王浩不可能仅关心个人的幸福问题。也因此,他常常陷于一种矛盾和痛苦之中:是专事象牙塔中的知识哲学研究,还是投身于更具实践关怀的思考和工作中。
例如,在《数哲》中他写道:“我们很快就能达到这样一种哲学观,它把哲学理解为关于如何缔造更好的社会的研究。有鉴于这一哲学观和当前的世界局势,我们不难理解如下的断言:当代知识分子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417页)
事实上,大约在写完《数哲》之后(准确地说是在1972年王浩第一次回国访问之后)的数年里,亦即七十年代,王浩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但这些研究没有为他带来满足,经过一段精神上的挣扎和苦闷期后,他很快就又回到了逻辑与数学哲学研究的正轨上去。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