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得以兴起的城市史研究,有学界先行者聚焦“长安”。《长安碎影》是著名学者王子今教授在“长安学”的学术旗帜下一份积极的参与,全书收录34篇文章,试图从几个以往人们关注不多的侧面描画咸阳,期望进一步有益于今人对秦汉历史文化打开总体认知,在其中“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导读”一章,阐明《汉代婚丧礼俗考》的许多论说,是以长安为背景的,可以看作长安学的学术基点,文章还追述了“训诂学第一人”杨树达先生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与铮铮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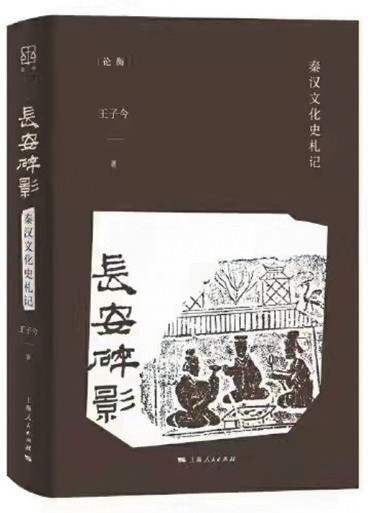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一脉,不尽薪火传受;学人百世,各有时代风格。如果回顾20世纪的学术创获,虽经历风雷霜雪,依然满山缤纷,令人目不暇接。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就是其中水边林下虽并不惹眼,却发散出异常清芬的一簇。
杨树达先生,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卒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杨树达考入时务学堂。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相继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教员。1920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农业专门学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文系主任。1926年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教授等职。

杨树达先生(1925—1928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字学概要、国学要籍、修辞学等课程。)
杨树达先生著说宏富,多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学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一书,作为20世纪学术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代表作之一,不仅被秦汉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视为必读书,其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也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老夫子以江河运行比喻历史演进的说法,被许多人所接受。历史确实一如江河,有“潮平两岸阔”的缓漫的河段,也有“绝壁天悬,腾波迅急”的峥嵘峡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节奏的差别,可以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历史印象和历史感受。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发表这样的感慨:“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反映了历史上文化节奏屡有时代变换的事实,反映了“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节奏急进的时代往往对于历史文化有较显著的推进的事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众所周知的乱世,但是以历史节奏分析的眼光看,确实实现了李大钊等人热情呼唤的“少年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中,几乎均是青年才士各领风骚。
我们说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少年”气象,学术创造也是同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于慧眼与卓识出版的集合近代学术大师名著的“蓬莱阁丛书”,我们看到已经问世的19种,这些专著最初出版时作者的平均年龄,不过41岁左右。杨树达先生也是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于乱中取静的学术生活中积累学识,发表论著,成就大器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说,史家的主要职责,是“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以发现和总结历史的“盛衰大指”(《十二诸侯年表》)。我们如果以较为宏阔的视界看历史文化的全景,那么,“盛”与“衰”,就并不仅仅是指王气的勃兴与凋灭,又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创造力总和的价值,意味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成就在人类智慧宝库中的比重,也意味着这一时期文明进步的速度。也就是说,如果进行历史的时代比较,不仅应当看到政治的“盛衰”,也应当对文化的“盛衰”有所重视。
或以为文章的刚柔,往往可以反映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唐代“国威复振”,“终有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西京相依。”(章炳麟:《菿汉微言》)然而,我们注意到,历史有政治的“盛衰”,又有文化的“盛衰”,政治与文化“盛衰”运动的波形,相互间未必可以完全印合。同意这一看法的朋友或许会接受这样的意见,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为极端的动乱纷争,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看作学术的盛世。
回顾中国近代学术史,可以看到杨树达先生以其勤勉的学术实践,为实现当时的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1年,杨树达先生完成《说苑新序疏证》。19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树达先生的《老子古义》二卷。这部书1926年又再版印行。1924年,《盐铁论校注》《汉书补注补正》与《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问世。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词诠》与《中国语法纲要》。《词诠》1954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高等国文法》,1931年出版《马氏文通刊误》及《积微居文录》。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杨树达先生著《中国修辞学》,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汉代婚丧礼俗考》。193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的《论语古义》和《古书句读释例》,北京好望书局出版了杨树达著《古声韵讨论集》。他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五卷《补遗》一卷,1937年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六卷增订本,1955年再次由科学出版社推出。
杨树达先生40年代面世的论著,有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春秋大义述》,以及讲义本《论语疏证》《文字形义学》《甲骨文蠡测撷要》《文法学小史》《训诂学小史》等。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经历了特殊的历史变化。而杨树达先生仍然“勤于述作,既速且精,诚令人钦仰赞叹”(周祖谟《致杨树达》)。胡厚宣也曾致书赞叹道:“深觉解放以来,关于甲金小学,惟先生著作最丰,发明最多,其贡献之大,盖突破以往所有之学者。倾仰之至!”中国科学院1952年出版了他的《积微居金文说》,1953年又出版了他的《淮南子证闻》,他的《积微居甲文说》附《卜辞琐记》亦于1954年问世。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耐林庼甲文说》附《卜辞求义》同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以《汉书补注补正》为基础完成的《汉书窥管》,1955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论语疏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的《盐铁论要释》由科学出版社推出。
对于杨树达先生的治学成就,学界评价极高。章太炎先生致书曾经夸赞道:“兄于治学可谓专精。”郭沫若先生亦曾致书言:“我兄于文字学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宾先生致书亦有“深佩卓见”语,谓“公在课程忙迫中犹能作专精研究,贡献古文字学者极大,敬佩之至”。陈寅恪先生致书亦称:“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于省吾先生致书对于杨著《积微居甲文说》也有“义证精确,发挥透彻,并世研契诸公无与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评价。胡厚宣先生也曾经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中发表赞语:“(杨树达先生)写文章最多,不失为五十年来甲骨学研究中最努力的一人。”
陈寅恪先生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又重复了“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的赞美之词,并且说:“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接着,陈寅恪先生又发表了如下一番感叹: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 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 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
陈寅恪先生所说“青山”“入梦”“白发”“浮名”,指1942年教育部公布杨树达、陈寅恪等先生为部聘教授,杨树达先生淡然处之,有“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诗句事。陈说揭示“功名”与“文化”之“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实在是极深刻的富有历史主义眼光的深见。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撰纪念碑文,有强调学术自立的名言:“……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50年代初,他在答复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意见时又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先生为杨著所作序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的称誉,亦体现了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肯定和坚持。有论者分析说,“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倒)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先生仍拟将陈寅恪先生的序言置于卷首,陈寅恪先生亦欣然同意。然而1952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致信杨树达先生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同年11月,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序文果然被删去。1952年12月6日,陈寅恪先生致杨树达先生的信中说到此事:“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和陈寅恪先生的序文出版时的遭遇,在他们风云变幻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是却能够反映其学术立场和学术品质。两位学者的性格虽有差异,但是就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则意志共同。因而所谓“铮铮有凛然之气”也罢,所谓“立场观点有问题”也罢,正反两种评价,其实是既可以针对陈寅恪先生,也可以针对杨树达先生的,尽管两位先生言行之风格的缓急刚柔确实有所不同。
一生淡于“功名”,“持短笔,照孤灯”“寂寞勤苦”“不少间辍”的杨树达先生在《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余性不喜谈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时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亦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昔年在京,往复论学之人有喜谈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错误之人如陈独秀者,与余虽未谋一面,然以讨论文字学之故,亦曾有书札往还。此等皆属学问上之因缘,与政治绝无关涉也。虑或误解,聊复言之。”虽然检讨了往时之见的“错误”,但是因“虑或误解”所作的解释,仍然使人感到内心与所谓“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畏政治如蛇蝎”的疑惧。
当然,所谓“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是人生的现实。学者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并不意味着逃避社会矛盾,放弃社会责任。以杨树达先生而言,抗战时期“何当被甲持戈去,杀贼归来一卷娱”(1939年12月24日诗),“却喜健儿能杀贼,故探圣典记攘戎”(《六十述怀》诗)等诗句,都深抒“杀贼”壮志,饱含救亡激情。他在1939年至1940年间开《春秋》课,所著《春秋大义述》一书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春秋大义述自序》)可知抗敌救国之热忱。其说其事,可以看作“故探圣典记攘戎”诗句的注脚。1946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消息传来,杨树达先生激愤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 书生论政,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悲恨之声,至今读来令人感动。
杨树达先生以“礼俗”确定研究的对象,原意当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而其中的礼仪制度,自然与通常理解的政制不同,实是一种因“俗”而生,又制约着“俗”,与“俗”始终存在密切关系的“礼”。“礼俗”,是社会生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然而,自50年代以来,“礼俗”,似乎已经退出了社会科学常用语汇。江绍原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礼俗迷信之研究》,于80年代末经整理出版,定名为《中国礼俗迷信》(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版),于是人们长期感到生疏的“礼俗”一语,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中。
杨树达先生作为国学大师,虽起初因语言文字学成名,于史学亦数十年积累创获,多有杰出贡献。1931年在清华大学任职时,从陈寅恪先生建议,“兼在历史系授课以避国文系纠纷”,与史学于是有了更为密切的学术关系。
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自序》中写道:“往岁余治《汉书》,颇留意于当世之风俗,私以小册迻录其文,未遑纂辑也。会余以班书授清华大学诸生,诸生中有以汉俗为问者,乃依据旧录,广事采获,成此婚丧二篇;见者颇喜其翔实,而予友曾君星笠乃见誉以为为史学辟一新径途,余知其阿好,未敢以自任也。”曾运乾先生所谓“为史学辟一新径途”,当然不是无原则的“阿好”,而是切实客观的评价。
读杨树达先生关于史料的论说,使人联想到傅斯年先生曾经强力主张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
傅斯年先生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讲台上教授“史料略论”课程,于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都曾经一再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30年代至40年代,他又发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反复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他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种对于史料的绝对重视,其实并非有的学者所说,是将史学和史料学完全简单地等同起来,从而否定了史学的思辨性和理论性,而是从史学之基础的角度强调了史学的实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对于史料的整理和使用,傅斯年先生提倡谨慎客观的态度。他指出,“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略论》)。在傅斯年先生的观念中,其实并不是以对于史料的整理搜罗而有意降低史学的价值。
傅斯年先生的主张,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但是真正按照这一原则从事史学研究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并不多。杨树达先生及其学术同志们实证主义研究的成功,正是实践这种对于“史料学”予以特殊重视的学风的典范。
(本文摘自《长安碎影》,王子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