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郝景芳选修了社会学系主任李强的“城市社会学”,听他讲城市分层理论。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李强提到,劳工群体是这些年经常受到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许正是这样的潜移默化,日后让她在《北京折叠》中创造出了“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
李强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十多年,后又主导了清华社会学系复建,担任该系系主任多年。他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018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在学术圈里他名字的前缀由“人大”换为“清华”,后又被亲昵地尊称为“强爷”。
2023年12月12日,李强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根基和最重要领域之一。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终身都没有离开这个领域。他的一生研究,仿佛都在反反复复地说:何以解忧?唯有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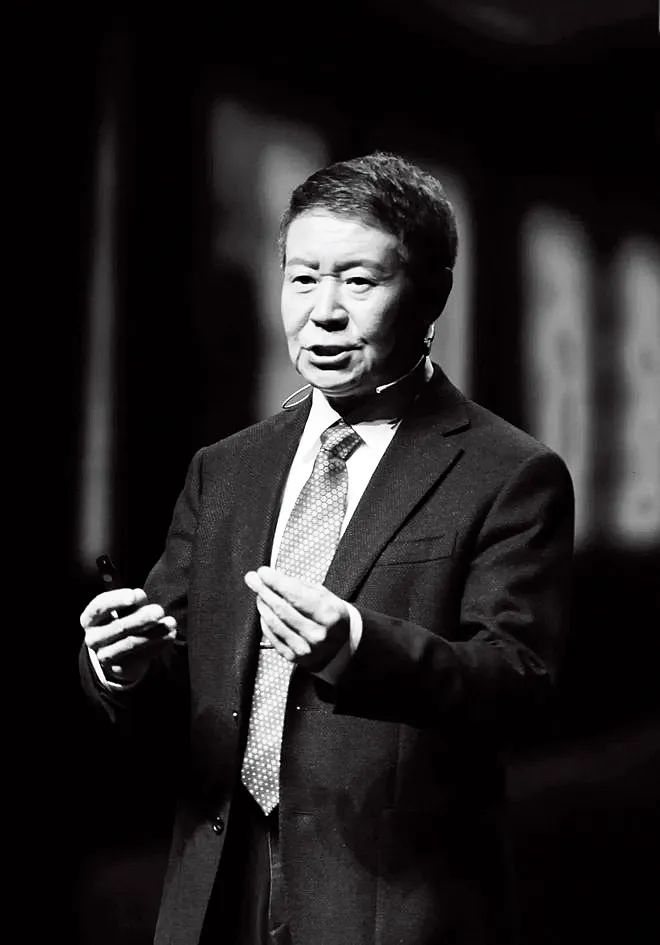
2016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教授在新清华学堂发表公共演讲:“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
“自学成才”
1979年的一天,在北京东四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外文图书展上,中国人民大学78级国际政治系学生李强发现了一整架归类为Sociology(社会学)的书,其中心理社会发展论创始人爱利克·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吸引了他,他想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
这是李强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也是他对这门引导人们“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学科发生兴趣之始。
就在不久前,邓小平提出,我们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忽视了多年,现在需要“赶快补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取消多年的社会学开始恢复与重建,国外学术专著被大量引进。
李强开始如饥似渴地读社会学原作。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停滞近30年,这个领域的书多是外文的,他英语基础好的优势就显露了出来。
他1963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中,一进校就发现这里藏龙卧虎,有些家境不一般的同学英语已“滚瓜烂熟”,他震惊之余开始疯狂学英语。直到1966年夏宣布取消高考那天早上,他还在背英语。“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9年。虽然这里地处“荒山野岭”,他却自费订了一份《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英文时政新闻周刊。
李强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硕士论文是关于西方的“白领阶层”,都需要大量查阅英文资料。光人大图书馆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他就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这里外文藏书很多,据说是全国唯一一家购书不受外汇额度限制的图书馆。
在人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间,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他大都读了,他的社会学基础就是这样靠自己读书打下的。
1984年,人大哲学系教师郑杭生从英国进修回国,在人大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李强找到他,两人一说即合,1985年李强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社会学所工作。
1987年,人大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郑杭生任系主任,李强任副系主任。郑杭生不久担任了校领导,虽然还兼着系主任,但具体工作多由李强主持。1990年李强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学,回国后不久,于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任命为系主任。
李强主持下的人大社会学系很包容。人大社会学系2000级硕士、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何晓斌曾回忆,当时人大社会学系是一个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李路路这样的学院派,有历史学者转型成性学研究者的潘绥铭,有在讲台上拿着发黄的手写讲义天马行空的徐向东,也有青年才俊洪大用、刘精明和陈劲松等。
“四个利益群体”
从硕士论文开始,李强就在研究社会分层。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人还不知有“社会分层”这样的社会学术语。
社会分层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概念,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各群体之间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制度化社会差异体系。那么,阶级与社会分层是什么关系呢?李强曾解释,社会分层是个包容性较强的温和的概念,阶级可以说是“属性差异”最为明显的社会分层群体,绝大多数分层群体都称不上阶级。
李强说,社会分层涉及平等与公平的话题,不均等(不平等)与不公平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均等(不平等)指资源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不公平则是指资源分布的格局不合理、不公正。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突出特点是“身份制”,或者说它的“不流动性”,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使其得以流动起来。
改革前,中国社会主要有四个大的“社会聚合体”——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革中这四个聚合体都发生了巨变。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受损状况,李强与孙立平、沈原等共同提出了“四个利益群体”之说,将社会群体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特殊获益者群体”从80年代到90年代有很大变化。“专业户”“万元户”等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1992年后一批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下海”,出现了一个经济精英集团。
李强认为,对“普通获益者”的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人们,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李强被任命为系主任时,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大潮高涨。在副校长郑杭生支持下,他在人大组建了“中国人民社会调查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前身。他多次采用PPS抽样方法,组织全国规模的社会学调查。这是一种等比例等概率的抽样调查,难度很大。
1996年,他主持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入户问卷调查,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1986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变化。结果,高达83.6%的城市居民和88.7%的农村居民回答生活“好了一点儿”或“好了许多”。
在李强看来,“普通获益者群体”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基础就在于此。这个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广泛,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获益群体,也因此成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大规模改制,一批职工下岗,从这个普通获益者群体中分离出去,进入了“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虽然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比起一些农村贫困地区可能相对还要好一些,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是强烈的。而上述农村贫困地区人群和其他一些最困难群体,就构成了“社会底层群体”。
改革中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这些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还谈不上是稳定的阶级阶层。90年代初,李强在研究中发现,国企职工是一个社会地位相当不错的阶层,无论经济地位、福利待遇还是社会声望都比较好。短短几年之后,一些人却面临下岗,生活下坠。但到21世纪初,改制完成,留下的大型国企又重新成为人们追捧的目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让李强深感震撼。
“复系一代”
1998年暑期刚过,清华大学负责抓文科建设的校党委副书记兼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显章和校长助理李树勤在人民大学见到了李强,邀请他加盟清华,主持社会学系复建工作。
改革开放后清华一直尝试复建文科,并于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院曾设立“哲学与社会学系”,但老清华传统优势的社会学学科没有独立建系。
李强收到邀约后犹豫了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学界征求同仁们的意见,没想到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去。而且,北京四中学生都有一个清华梦,他的这个梦是被“文革”打断的。1999年9月,他接受邀请,正式调入清华大学。2000年,社会学系在清华复建,他出任系主任,兼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系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挤在清华文科北楼两间办公室办公。楼里挂着清华社会学先贤们的画像,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李景汉、李树青、陈序经、吴泽霖、杨堃和费孝通。李强专门拜访了费孝通,汇报了社会学系复建情况,费孝通说:“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
孙立平、沈原等社会学研究者纷纷加盟清华。沈原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过科研处长,对学科建设很有想法,一再强调要研究社会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孙立平原是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强为了邀请他加盟,和校领导积极沟通,不走职称评审流程,教授职称、博导、住房一并解决。孙立平历来最不愿意做管理工作,进入清华后几乎天天到系里,积极参与讨论,写学科规划文件。
李强与孙立平、沈原等讨论后为清华社会学发展确定了三个重点方向:一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这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二是城市社会学,因为清华工科很强,城市研究基础雄厚;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景军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景军是哈佛大学博士,放弃了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国。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大牌教授,因此他进清华后开拓了医学社会学。
清华社会学系复建初期没有博士点,在两院院士吴良镛的建议下,李强在建筑学院规划系招收了博士生。有一段时间,社会学系的博士生补齐规划专业课后拿的是建筑学工学博士学位,这些毕业生后来在城市规划界突出了社会规划特色。
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张小军、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裴晓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郭于华等也纷纷加入清华社会学系,各自开拓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
那时清华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队伍,社会学系很长时间坚持了这个原则,保持着十来个教师的规模。这个精干的团队个性十足,“一个顶一个”。熊知行楼里经常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偶尔大嗓门的争执声。李强则没什么锋芒,总是和和气气,云淡风轻,把人事行政和后勤方面的琐事都承担了,让老师们能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赵鼎新曾评价,清华社会学系“复系一代”是一批极具个性和学术眼光的人物,而李强却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几年内就为清华社会学系开辟出一片天地,令人赞叹。
清华社会学系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该系名列社会学学科第三名,打响了名头。

李强大学时代留念。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网站
面对真问题
李楯说,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社会学界在决策咨询中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期。
那时,清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由李强兼任,执行主任为沈原,副主任为谭深,李楯任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李楯说,得益于李强的人脉和领导力,研究中心搭建起了由一百多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网络。
那时研究中心经常召开“圆桌会议”,邀请党政官员、经济界人士、媒体、研究者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参加,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中心与环保总局有过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参加过紫坪铺等工程的评估,为水利电力部做过《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做了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调研。
李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北京社会学界形成了以北大、人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为主的专家群体,李强在专业方面或许不见得是最强的,但以木桶理论而言,他最为均衡,所以能装的水最多。他待人友善,善交朋友,人脉远远超出社会学界,因而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处理好“三校两院”之间以及与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等官方研究机构的关系。
清华社会学系提出了“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问题”的建系宗旨。在中国社会学界的诸多学派中,清华社会学系以实证学派见长。这与历史传承有关,老清华社会学系的费孝通、陈达、吴景超和李景汉等都是长于田野调查的学者。李楯说,前辈学人常称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进入清华之后,李强不再经常组织大规模全国性调查。他觉得,这种调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搜集数据,对于数据的分析利用反而不足,不如聚焦于社区,更多开展解剖麻雀式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
他采用中国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总体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结构。丁字的一横代表着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群体,一竖则代表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系列人数很小的群体。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成了“土字型”。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有了明显增长,一部分人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进入了中间层。
“土字型”社会结构的出现无疑是社会结构的进步和优化,但处于下层的社会群体比例仍然较高,离较为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有距离。
李强提出,制约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四个世界”,即“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这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除人们所熟悉的城乡差别外,中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
根据2010年的《中小城市绿皮书》,城市的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见,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或“土字型”,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超大城市则已接近于“橄榄型”。
李强认为,当今中国城市可以明显区分为“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两个世界。这使得新兴中产阶层产生“天花板”和“区隔”心态。最新研究证明,当代全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沮丧的中产阶层”。同时这也说明,我国社会实际上还沉淀了大量的资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打破“四个世界”的分割,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社会经济就有望获得更大发展。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设想的三个空间的人口数量是,第一个空间500万,第二个空间2500万,第三个空间5000万。即第一空间的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6.25%,第二空间为31.25%,第三空间为62.50%。2016年在“人文清华讲坛”与李强和作家格非对谈时,她笑着承认,这个比例是她“拍脑袋”想出来的。
李强表示羡慕小说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这要是放在学者身上那就叫伪造数据、学术不端了。他以社会学家的严谨认真测算了一下,看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他说,按照书中描述,不同空间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这类似于社会分层中的“职业分层”。他引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出,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职业上层人数占11.3%,中层占41.4%,下层占47.3%,不是太吻合。但如果是一般城市,那么职业上层的比例是12.67%,中层是38.44%,下层是48.89%,跟《北京折叠》中的三个空间更接近一些。
李强说,所谓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的核心问题是不能共享。这给我们的启迪是,不要造成空间的封闭,有差异、有贫富都没什么关系,只要在同一个空间里,有畅通的流动渠道和上升通道,社会就有希望。
“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李强曾说,要想预测未来,最好还是看看历史。回顾20世纪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只有四个字可以描述:沧海桑田。
或许因为总是把眼光放在这样一个长时间段下,他有一句经典口头禅:不要急,不着急,慢慢来。
他说,社会科学在中国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沿革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逐渐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同“人文”混淆。频繁使用的“文科”一词,不仅混淆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也混淆了社会科学与应用文科(比如商、法)。他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
他坚持清华大学要办社会科学学院,认为社会科学都是通的。香港很多大学都采取这种模式,社会科学只分领域,不分学科,因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统一。2012年,他出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
2014年,他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他认为,社会学论文的核心必须以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实证研究往往又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这对学生非常重要。绝大部分社会学学生论文都是以一个社区为基础,做比较长期的实地调查,这个学风从费孝通那代社会学者就开始了,燕京大学的许世廉教授等人就搞了“清河实验”。
近年里,本科时有“小钢炮”绰号的李强身体渐渐虚弱,但他从未停止工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回忆,在最后的日子里,李强常与弟子促膝长谈,稍有余力仍谋划不止写作不休,去世前十天仍有论文问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李强的离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他才73岁,大家认为这正是做更大学问的年纪。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发文悼念,称李强为“拥有能够展望中国之未来的睿智和慧眼的社会学家”,他的离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东亚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
在八宝山送别李强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现任雀巢中国业务总监的刘洋与同学敬献了花圈: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洋解释,“已识乾坤大”是指,李强老师家学渊源,后成为学界巨擘,也是政府高参,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数人,对社会底层逻辑和高层布局的了解也超前于大多数人;“犹怜草木青”是指,他一直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对事物规律抱有真诚的好奇,对社会问题抱有真切的关怀,对学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关注着“新清河实验”的进展,嘱咐学生坚持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刘洋和她的同学们都觉得,李强老师当得起此语。
(本文参考了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周晓虹《重建中国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