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炳棣
196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何炳棣,虽然不常在“中研院”工作,但他作为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人社中心)通讯研究员,每每在两年一度的院士会议前夕,会先到人社中心待上一阵子。梁其姿教授作为人社中心行政工作的领导,和他有比较密切的往还。彼此相交,何炳棣的行止,让梁其姿教授等同仁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一个“老虎”的外号。这固然是对他“具备老虎的战斗精神与顽强意志”的赞誉(梁其姿,《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页30);其实另一方面,何炳棣臧否人物,较诸老虎之凶猛,也不遑多让。如他对另一位考古学名家、长期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院士,全无好评,说张“旧学根基不足,成见甚深,瑕瑜莫辨,对哈佛大学的汉学及传统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负相当责任的”(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297-298)。“老虎院士”之名,不胫而走。
然而,何炳棣绝对不是“书呆子”;他在学界里的应对进退,自有“本领”。还只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的他,1953年中旬首度拜见已经是美国哈佛大学名牌教授的费正清之际,“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不料,费正清却回答他说,因为张德昌比早他半年引用了这部书,所以他只能排到第三位(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45)。
只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回顾《筹办夷务始末》的引用史,无论是何炳棣的“恭维”,或是费正清的响应,费正清和何炳棣的定位,都不是历史事实。
由大清帝国咸丰皇帝之“帝命”而开始纂修的《筹办夷务始末》,基本总汇了帝国对外关系的档案文献。1929年夏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发现道光、咸丰二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复由昭仁殿寻得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经外交史名家,尔后从政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建议,于1930年1月影印出版(张志云、侯彦伯、范毅军,《了解中西交往的关键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与流布》),从此就如蒋廷黻所言,掀起了“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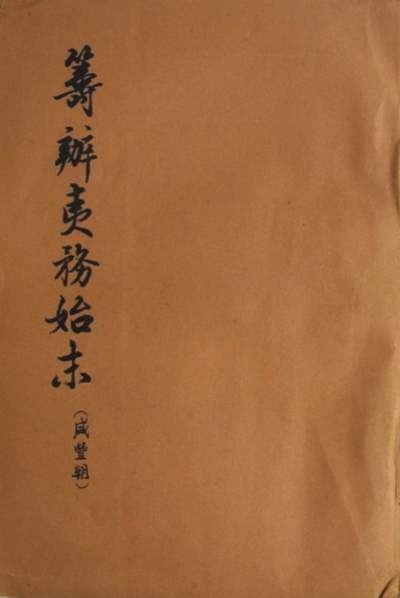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书影
回顾费正清本人的学术生涯,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大学部最后一学期的时候(1929年春),遇到了以研究外交史而著称的韦布斯特(Charles K.Webster),后者在印章社(the Signet Society)的午餐会上向费正清等听众宣告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及其意义。在韦布斯特的建议下,不懂汉语的费正清,以初生之犊的勇气做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决定,开展了让他觉得兴奋刺激的冒险历程(exciting enterprise)。不过,费正清首先捧读的是马士(Hosea B.Morse)三卷本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间出版)。要到了1932年,费正清抵达中国留学以后,他(透过韦布斯特的介绍)与蒋廷黻接上线,方始看到了这套书;在蒋的指导下,读之览之,竟尔在1933年发表了第一篇结合使用中英文档案的学术研究论文:“The Legalization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从此展开了他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事业。
费正清的学术生命,固然与《筹办夷务始末》关系密切;在具体的历史场景里,他引用这部书的自我定位,却是大谬不然。
就史料整理与发表的面向言之,《筹办夷务始末》始终是选择去取的标准模板。当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故宫里发掘出各式各样的资料,即以《筹办夷务始末》作为是否应公之于世的权衡标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军机处档案,“时复发现外交史料,有未载入《夷务始末》者”,故假《故宫周刊》之篇幅“陆续发表”;故宫于1930年3月开始出版的《文献丛编》,也声明曰,凡所刊布之文献,亦都注明凡可见诸《筹办夷务始末》者皆不著录。一般史学工作者遇见新的数据时,也会取之相核,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关瑞梧即与《筹办夷务始末》相比较,即发现有未见诸其书者。
就《筹办夷务始末》作为史学研究基本材料的面向言之,目前还不知道张德昌的哪一篇文章引用了《筹办夷务始末》;但是,在费正清的论文发表之先,在蒋廷黻以外,已有学者利用这部书撰写学术论文了。像是陈文进述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源由和经费来源,即引用了咸丰与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就历史教育的面向来说,如1930年度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外交史”课程的教师(可能是陈恭禄),就将《筹办夷务始末》列为参考书。它还可以成为史学后进开展史学训练历程的对象,如燕京大学历史系1932年的毕业生张汉臣,就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指南(咸丰)》作为学士论文的题目,应该也对这部书花了一番功夫。
美国史学界也很快就揭示了《筹办夷务始末》出版的消息。中国留学生郭斌佳(Pin Chia Kuo)即在1931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撰文简介,说这份文献提供了别处不能发现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翌年,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皮克(Cyrus H.Peake),同样在《美国历史评论》撰文述说20世纪20与30年代新发现的各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料,也指出如果细心研究《筹办夷务始末》,必然可以澄清中国国际关系里许多幽黯难明的阶段,也可以促成更为充分与详尽的著述的问世,他并举蒋廷黻撰述的各篇英文著作为例证。
显然,在费正清之先,《筹办夷务始末》已然是(中国)学界广泛利用的数据;在这波新起的“史学实践”浪潮里,留学中国的费正清,其实只是盛逢其会的弄潮儿之一而已(参考潘光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
何炳棣于1954年得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捎来的好消息,知道自己“拼命”完成的英文巨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已被列入“哈佛燕京专刊”,为自己打进美国“第一流学府”增添无限机会。且杨联陞在这封信里,谆谆劝告何炳棣对于“某位误释明代人口数字准确可靠的学人,评语不可太厉害”,因为“老虎亦有打盹时,若自己小辫子被人抓住,亦甚难受也”(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286-287)。无论何炳棣是否接受了杨联陞的劝告,一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号称“老虎院士”的他对费正清的“极度诚恳的恭维”,都被后来者抓住了“小辫子”。
至于费正清,身为一代学界“霸主”,也不是无疵可议。任教哈佛的同事杨联陞,曾经以“霸”字形容过他,又说过费正清擅于“纵横捭阖”。费正清的同事回忆说,当年在以费正清为领导人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里,在收发柜台上的两个文件盒上,分别写着“上谕”和“奏章”,凡是由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叫“上谕”,收进来的文件则是“奏章”。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心的“大家长”的风范,可见一斑。然而,“一言九鼎”的大家长,不会没有失察的时候。
何炳棣和费正清都是第一流的史学家。然而,严格地检证两人之间的答问,揭示历史的本来样貌,正可证明,不论是“老虎院士”抑或是“霸主”,他们的“夫子自道”,实非准确。“老虎亦有打盹时”。有志研史问学的后来者,岂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