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百年历史上记载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兄弟故事,比如冯友兰与冯景兰,闻一多与闻家驷,朱自清与朱物华,费青与费孝通,潘光旦与潘光迥,萨本栋与萨本铁,冀朝铸与冀朝鼎,钱钟书与钱钟韩,庄逢甘与庄逢辰;再如三兄弟的胡敦复、胡明复与胡刚复,熊大仕、熊大纯和熊大缜,曾昭抡、曾昭承和曾昭德,袁复礼、袁同礼和袁敦礼,吴征铠、吴征鉴和吴征镒,时昭泽、时昭涵和时昭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同在清华的四兄弟:梅贻琦,梅贻琳,梅贻璠和梅贻宝!而在清华政治学系,余日宣与余日章,萧公权与萧邃,邵循正与邵循恪,则是众人耳详能熟的手足。

那些年,清华园中有一对兄弟,他们的生命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都生于1897年,都在出生后离开当地,都就读于教会学校,然后都考入清华、进入密苏里大学,而且都回到南开、再到清华任教,最后又都离开故园,终老于美国。兄弟两几乎是前脚跟后脚,亦步亦趋地走过了几十年。所不同者,是兄活得短一些,弟活得长一些;兄重在立功,而弟重在立言。这对兄弟,就是萧蘧与萧公权。

坐者为堂兄萧蘧先生,站立者为萧公权先生
家世学业堪相酹
萧蘧[qú],字叔玉。也许是蘧字过于偏异,因而当时的师友弟子亦经常直称萧叔玉。他与萧公权都是江西泰和人,但萧蘧生在蜀地,后来随家迁到沪上;而萧公权生在南安(今大余),后来迁往四川。萧蘧留下的文字实在太少了。隔着历史的重重烟云,后人看得更清晰一些的,只是萧公权的足迹与心迹。
萧公权6岁时,在四川开始读经史,13岁开始学英文。14岁始学日文。19岁那年的夏天,萧公权考进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入三年级,从叶楚伧学国文。1918年6月,萧公权考进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以中学毕业生的资格考入清华高等科三年级,实非寻常。萧公权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却与他的八哥萧蘧的鼓励有关。因为在此之前,萧蘧本人已于1916年考入清华高等科四年级。他对萧公权说:“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无论如何,你必须一试,纵然不取,于你并不损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萧公权当然也就不客气。当他接到清华学堂录取通知的时候,萧蘧已准备要放洋了。与萧公权同属庚申级的学子中,人才辈出,其中有陈岱孙、刘驭万、刘师舜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萧公权与同学合办《晨钟》日报,包括时评、社论、新闻、小品文、广告等栏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萧公权与同学也很是出了一些风头。当然,最出风头的还是罗隆基和陈长桐。罗隆基是清华活跃分子之一,每逢当众演说,他极尽慷慨激昂之能事,于是被列在北洋政府逮捕的名单里,他立刻决定走为上计,在身强力大的清华运动员时昭涵保卫之下,冲出军警包围的天安门,向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节的特区“落荒”而去。“时昭涵威震天安门,罗隆基独走交民巷”,这一联语名闻一时。与这位“八年清华,三赶校长”的罗隆基相比,萧公权显然是另一类型。在清华期间,萧公权的政治观已日趋定型,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的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
1920年夏,萧公权自清华学校毕业,赴上海办理出国手续。8月23日离沪赴美求学。与当时许多远洋邮轮的乘客一样,途经日本时,萧公权与同学全数上岸到横滨与东京观光。他发现当地街道整洁,人们也普遍有礼貌守秩序,坐共享电车都自然地、自动地,按到来的先后次序在车站排成一列;电车来后,也是先下后上,决不拥挤。“这的确是国民教育程度的表现”。此前他与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大看得起“东洋人”。此时却被东洋人好好地教育了一番,已开始修正轻视“小日本”的态度。后来萧公权在密苏里大学时,同期肄业的远东学生,除了了十几个中国学生之外,有两三位菲律宾人,他们专爱找美国姑娘;惟一的印度人则喜好放言高论。三个日本学生则潜心学习,毫不外务,生活亦极为朴实。他于是更意识到日本青年的不可轻视。他想:“如果日本青年人大部分都像这几个日本留美生一样,这个岛国的前途未可限量”,那种看轻日本人而不自策自励的心态是错误的。
9月,萧公权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但很快便发现自己并非是做“无冕之王”的材料,因而转入哲学系,以郝真教授(WilliamHudson)与余宾教授(George H.Sabine)为导师。多年之后,他仍为此而庆幸,因为若非如此,他自己很可能只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名小卒。在密苏里的三年中,他不仅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而且选修了德文、法文、植物学等课程。按照密苏里大学的规定,本科三年级以内必须参加英文程度测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萧公权和几位清华同学都顺利通过,而有些美国学生却居然不及格。同期在密苏里大学的中国同学实在不少,他所熟悉的就有杜钦、李干、陈钦仁等,当然最熟悉的还是萧蘧。萧蘧1920年入该校研究院后,因成绩优秀一年之后就获得助教职位,这在该校的中国同学中是为首例。在此后的一年间,萧公权与八哥合住在一家私人住宅里。这虽比学校宿舍更多费一些银子,但能够很好地融入美国的日常生活,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次年夏天,萧蘧就转到了哈佛。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样选修经济学、交在日后成为清华同事的陈岱孙。当然,相比这位帅气的小伙而言,他的成绩可能要差一些,但同在哈佛,已经是足够优秀了。
1922年夏,萧公权自密苏里大学本科毕业,因成绩优异,被选入全国性荣誉学会(PhiBeta kappa)。秋天,他入同校哲学系研究院攻读硕士,副修心理学;1923年,萧公权完成硕士论文《多元国家理论》(The Pluralistic Theory of the State),于6月获硕士学位;9月,萧公权转入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院,主要受业于狄理教授(Frank Thily)。绮色佳是纽约州的名镇之一,是一个大学城。此地风景清丽,纤尘飞不染,宛有江南山水之味,就在这美好的自然环境之中,在良师益友的启迪切磋之下,愉快地度过了他的三年学子生活。
萧公权在婚恋问题上与他的学长胡适颇为相类。1921年夏,当萧蘧等人离去之后,有位适龄的女子来到了密苏里。这时的萧公权已是对学校情形最为熟悉的中国同学,自然要代她去寻觅住所、办理报到注册手续。翌年,她又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来绮色佳度夏,结果二人几乎天天见面;天气晴好时,还会一起外出观景。很多人便以为二人已进入罗曼蒂克的阶段了。萧蘧风闻后,立即要乃弟与在家乡已聘定的未婚妻通信,并做通其岳父的工作,允许这对未婚夫妻相互联系。但他的族侄庆云却极力“劝进”,鼓励其不要受传统因素的束缚,另寻新爱以免日后追悔无及。对此,萧公权表示:“就见识、性情、容貌各方面说,她确是一个动人的女子。她和我虽有浓厚的友谊,却并不好踏入恋爱的境界。她早知道我已订婚。……”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罗曼蒂克当然再无开展的可能了。在这一点上,萧公权也很敬重胡适。1925年,他应康奈尔大学教授H.S.Williams之邀登门造访,见到了他的次女,也就是当年胡适在康乃尔时的女友韦莲司。这位奇女子恳切地打探胡适的近况。此时的胡适在中国学界已然如日中天,远在美国的萧公权也不会对其风头毫无所知。他报告了他的情况后,女子说He is making history(他正在创造历史)。萧记录了这次会面,并且对此一评断深表赞同。
1924年,在主修系(哲学)、副修系(政治)的各门考试以及法文、德文的考试之中,萧公权都一帆风顺地通过了。1925年初夏,萧公权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几经挫折,他终于在1926年5月初完成了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导师颇为满意,恺德林教授进而介绍给伦敦奇干保禄书局出版。彼时的中国留美生,自胡适开始就惯于投机取巧,常以研究本国的题目而挣得学位,文科生真正研究西学者并不多;能因此而出头者,更是屈指可数,萧公权是其中之一。6月中旬,萧氏参加康乃尔大学毕业典礼,获博士学位。
相对于堂弟按部就班、顺风顺水的求学生涯,萧蘧的受教之路却要更加特别一些。在哈佛读书期间,萧蘧师从经济学家陶锡阁(Taussig),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后,他着手写作论文。但一件偶然事件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中国留美同学会的会长卷入一桩假支票案件,被查获并遭逮捕。最终,检察官同意和解,但是勒令遣送该生回国,同时要求有人监护,以保证该生确实回到中国。当时实在无人愿意出头料理此事,萧蘧只好表示他可以护送这个同学回国,并和导师商妥回国事宜,陶锡阁也同意他回国做论文。然而,他在1925年回国后旋即被南开大学聘为教授,并任文法学院院长等行政工作,因而后来一直没有完成博士论文。
教坛学坛各成荫
1926年8月中,一个半阴半晴的日子里,“麦金利总统号“在风平浪静的上海靠岸。萧公权与其他八位同行回国的留学生说了声再见就分别了。他从此在南方大学与国民大学担任政治学与社会学课程。这是当时两所不入流的“野鸡大学”,学生程度不高;那些既考不进公立南洋大学,也考不进私立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只好来这里混文聘。而这类学校为了赚钱,也乐意多招学生。
不过在上海时,萧公权却三喜临门:一是他完成了终身大事;二是他终于摆脱了“野鸡大学”的教职,获得了较为可心的聘书;更重要的是,他接到了英国的著名出版商的来信,决定将其博士论文付印,并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后来更被牛津大学曾指定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之一)。他喜出望外: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已是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梁启超、罗素、柯复嘉等比肩,更是无上殊荣。恰在此时,他再一次接到了先驱者八哥萧蘧的召唤,来到了南开大学。此时的南开,规模不大而地位不低,在此任教的除了有萧蘧,还有何廉、蒋廷黻、李继侗、姜立夫、饶毓泰等学界好友。群贤毕至,南开风光一时。但在1929年,萧蘧与蒋廷黻、李继侗等相继弃南开而赴清华。几位台柱的相继离去,让校长张伯苓措手不及,但对此既成事实,他无法改变。萧公权曾回忆说,私立南开的经费紧张,经常欠薪,教授同人往往处于入不敷出的困窘之中。恰在此时,萧公权也接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当时该校是新办大学,校长是张学良,银子多得惊人;那里的清华同学也多,如陈钦仁、孙国华、张忠绂等等。萧公权正好想去关外游历,因而毫不犹豫地应聘了。此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此任教,少帅张学良对林夫人表示了特别的兴趣,二人当然不宜久留,匆匆返回清华。此是后话。
但萧公权的机会也随之来到了。1930年春天,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欧游回国,经沈阳时特地来看萧公权,约他去燕京大学任教。萧公权本来就只打算在东北待一年,此时接到燕京聘约,当然乐意接受。燕京也是名校,但却是教会学校。这位早年毕业于教会中学的教授,再次与教会学校结缘。秋天,萧就任燕京大学政治系教授,负责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等课程。燕京又是典型的美国式大学,而按美国大学的规矩,各系“概论”课一般由系主任亲自担任,以便奠定学生研修本系其余课程的基础。徐教授将此课程让给他,足见其推重之意。1931年夏,萧公权在徐办公室里商谈课业时,一个新招收的一年级女生表示愿进政治系。徐说:“你去选修萧教授的‘政治学概论’,能够及格,我便让你进政治系。”徐对萧的赞赏于此更是显露无遗。
燕京很洋气,待遇也优厚。当时,在整个北中国,胜于燕京的学校几乎没有。作为一个学术新进,获得燕京教职也不能算是容易,萧公权于此当然有久留之意。但在1932年上半年,他接到了清华政治系主任浦薛凤的任职邀请。这的确让他怦然心动。燕京的条件已够好了,水平也不低;而清华条件更好,水平更高。他当然不能不动心。但初来燕京又要他就,无论如何有点“那个”。这时系主任徐淑希正在国外休假,他找到了燕京政治学系代理主任且兼任清华政治学系访问教授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orwin,对方坦诚说:“为系里着想,我不愿让你离去;为你本身着想,清华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既然这样,萧公权找到了燕京法学院院长,退还了续聘聘书。这一关键性的抉择,开启了他日后的黄金岁月。
清华政治学系本就有浦薛凤、张奚若、钱端升和王化成,又有萧公权加盟,稍后还有陈之迈到来,阵容当然极为强势了。何况校内还有包括八哥萧蘧在内的一班南开旧友。于是,任教清华成为他终身难忘的美好时光。他每周六小时授课,又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研究。之前已将重点转入中国政治思想的他,此时又回过头来担任了西洋政治思想课程。1934年夏,蒋廷黻受蒋介石委托,借休假之机访问苏联和欧洲,他所主编的The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季刊委托给了萧公权。萧公权为此整整代理了一年。蒋廷黻是极为入世之人,从事此类事务是性之所近,但对于书呆子性格的萧公权实在不是易事,吃力却未见讨好。直到1935年8月,蒋廷黻回国,他才卸下了编辑的责任。另外,他常来往的还有蒋廷黻、浦薛凤、李继侗、吴宓、孙国华、赵守愚、陈岱孙等。当然,晤谈最密切的是吴宓。吴宓当时是久负盛名的“情圣”,尤以“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岛四海共惊闻”而名动京津。身为旧式人,却贪恋新派婚恋,当然是自找罪受。此公在波澜起伏情海之中阅人无数,但最终空手而归。相形之下,甘于平淡婚姻的萧公权,倒是和和美美地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清华园,他仍然与八哥萧蘧密切交往。萧蘧和陈岱孙、蒋廷黻等一样,都很洋气,很喜欢去骑马和郊游;相比之下,堂弟就文气多了。萧公权是个本分的读书人,而萧蘧则曾是煊赫人物。他在1930年至1934年曾担任清华的经济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及教务长,主要研究经济学、国际贸易和金融;又与马寅初、李权时同被选为中国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三大台柱”。
萧蘧有才学,有能力,也有个性。他恪守原则,不太在乎个人名利。当时“在清华,关于如何治校,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萧蘧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他想用美国办大学的方式在清华治校。”但一些教师却有不同的主张,萧不肯让步,不少年轻教师就合起来“把他选下来了”。当时在清华访学的费正清则说:“萧蘧很热忱,非常重视培养年轻人,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想在留在中国,对中国有更多的认识,他聘请我在清华当助教,并指导我如何深入了解中国”。
那时的清华,的确是中国学界的“天之骄子”,有着第一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萧氏兄弟的确是享受了几年的“清福”。萧公权日后对此念念不忘:“清华五年的生活,就治学的便利和环境的安适说,几乎接近理想。”萧家五口初到清华时住在老南院二号教职员住宅里。萧蘧家住在六号,相距很近。一年后,新南院落成,他们迁居六号。这是西式的砖房,极为宽大。电灯电话,冷热自来水等设备,一概齐全。陈岱孙是其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也住在左近。这样,谈学文论艺,好不惬意。他当然舍不得这“天堂岁月”。1933年,朱经农约他会沪上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并未答应。不过,曾在清华呼风唤雨的萧蘧,却已一度离开学校了。
随着学术作品的先后刊印面世,萧公权已声名日隆。抗战前夕,在外侮日益迫近的情势下,学人一心学术报国,磨剑砚池,意在发掘祖国文明,力证文化久远。其中汤用彤的《魏晋南北朝佛学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都在酝酿之中;清华学人更在奋力原创,此时冯友兰完成了他的《中国哲学史》、蒋廷黻在准备他的《中国近代史》、萧公权也在酝酿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陈寅恪的“隋唐三稿”、张荫麟的《中国通史》亦在发萌之际。这一切,都使清华蜚声中外。此时中国亦成为除北美与西欧之外“世界上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地方”。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外间形势也越来越恶劣。恰在此时,掌管庚款支用的中国文化基金会于1937年为充实内地的高等教育,决定在四川大学设立庚款讲座教授。杭立武出面邀请萧公权加盟。但正当萧公权与赵守愚束装待行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当日清晨日军飞机轰炸南苑驻军营房,清华园可以清晰听到枪声炮声。一日下午,清华图书馆前甚至落下一枚直径四寸的炮弹。
美好的清华岁月无疑来到了尾声。晚年的萧公权,曾对他在清华五年的“天堂岁月”念念不忘:“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好设备都最好。”在此的教学成绩,“当然不坏”。这“再造”的大恩是无法忘却的。
正如清华五年对蒋廷黻的意义一样,这五年,对萧公权来说,也是奠定其毕生大师级地位的关键时期。在抗战爆发后,他和诗友吴雨僧等一样都挥别了清华园;但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南下经过汉口时,他又见到了他的老同学、时任汉口市市长的吴国桢,以及无冕之王、报界闻人陈钦仁。后者的境遭曾是他当时求学密苏里大学时最初的梦想,但此时此刻,他们却无法细述当年的共同经历了。
浪迹南国天地间
南下后,萧公权重游蜀地,担任了四川大学教授。校长程天放曾力邀他担任政治学系主任,但未获允可。从1938年2月到成都,萧公权一直住到1947年8月,长达9年半;加上此前曾渡过的11年,他在四川前后住过23年。因此,有人甚至将他视为蜀人。滞留四川期间,他曾在川大、燕京、华西、光华四所大学任教,也曾应周炳琳之邀,到中央政治学校做“党权与国力的演讲”,1944年夏,他应邀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任教官,为时约一个月。同期任教官的还有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等人。这也是“命题作文”,训练团命萧讲“各国政治思想”,而钱端升讲“各国政治制度”。结果,钱端升讲到了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的运用和效果问题,纵论天下,挥洒自如;萧公权的这位清华前同事是一流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但在这里讲这些内容,实在不合时宜,结果招惹了不少反感。旁观者经常讲,这个一心仕途的人,实在不内行,过于“天真”。反倒是无心政治、以书呆子自诩的萧公权在训练团讲得滴水不漏,没有造成反感。当然,他也无法讲到钱穆那样的极受欢迎,因为他对传统并非不加分辨地倾注过多的“温情与敬意”。

说起来,萧公权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立志不做“官”,专求“学”。抗战前夕,学者从政浪潮袭来,甚至在堪称世外桃源的清华也造成声势。其好友蒋廷黻就在此时进入政府。抗战爆发,学者从政更形普遍,而这样的馅饼也落到了萧公权的头上。1939年1月,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张群决定延请学者加盟,清华政治学系的浦薛凤、王化成就应邀就任参事。吴国桢也代张群转达了对萧公权的期望,并说即便不就政职,也希望到重庆谈谈。萧到重庆后,蒋廷黻要其在官邸下榻,自然要讨论一番学术,而且对他“谨守教育岗位”表示理解。张群约他到官邸午餐,十分恳切殷勤。回蓉后,萧再次致信吴国桢替其陈情。于是,平生惟一从政的机会就此错过了。1943年,在重庆开会时,陈布雷又来见他,邀其入党,而他的表示是:自己以非党员身份发表建设性的提议或善意的批评,似乎尚为一部分人所注意;“假如我以党员的身份来发表同样的议论,读者未必会加以同等的重视。”听到这一番话,陈点头说“很有道理”。于是萧又放过了一个加入国民党的机会。
但萧公权并非对国事漠不关心,事实上他在蒋廷黻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小尽“书生报国”之责,有时用本名有时以用笔名,比如“君蘅”,比如“迹园”。他的“立言”宗旨是:“把平日所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为了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他还成为当时政制改革的咨询专家。他曾专门为此进行相关的考察,但他却从中发现不少令人难以满意的现象,例如成都参议员选举的时候,“选民”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有的一人手里拿着十几张甚至几十张票。这倒在其预料之中,不可思议的是,开票时发现某区所投票的总数竟超过该区登记选民的总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首善之区”尚且如此,别处更可想而知。这让萧公权意识到,推行宪政,远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有赖于加强对民族的教育,因“教育的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这些年里,萧公权写完了他一辈子的一大半的政论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收入了1948年出版的《宪政与民主》之中。
诗以言志,在抗战的困苦中,萧公权并未放弃早年做诗的兴味。1940年夏,萧公权接待了回成都省亲的老友朱自清,二人自然又是一番诗歌唱和。但与萧过从更形密络的还是吴宓。吴因在西南联大与陈福田等相处不洽,愤而离去,转到燕京任教。此时同在该校任教的还有陈寅恪、李方桂。他们都是学界名人,也都是清华旧友,外人便以“四大名旦”称之。那时的诗友实在不少,有的是“职业文学家”,有的是“业余诗人”。萧公权在诗道上无所偏倚,诗兼唐宋之美。他诗才过人,却自称“我学诗是想培养能力去做比较像样的诗,但我绝不想去做诗人”,因为“自己短少做诗人的天赋”。自己作诗很多,但“成绩欠佳”,只能说“其志可嘉”。在这战火纷飞之际,居然还能诗酒临风,直可谓“苦中作乐”。在成都期间,萧公权做诗五百多首;而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总算下来也不过二百多首。

当然,在蓉任教期间,萧公权最为重大的功业,便是完成了使他闻名遐迩、名留学史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这既是他极为得意的力作,也是呕心沥血的作品。此书的写作时间仅有两年,但为了酝酿此书,萧公权准备了十多年。早年打下的国学底子,留美时所接受的严格全面的政治哲学训练,归国后长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学经验,使萧公权具备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中西融会、古今融通的全才;加之在清华期间所编纂的长达1400余页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数据辑要》,作为撰写之基础数据;萧公权的最后着笔几近水到渠成之举,1937年,萧公权的美国导师畲宾教授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Political Theory)一书,名噪一时。也许是受此启发和鼓励,萧公权于次年开始了他自己的写作,并在两年后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师徒二人东西辉映,而所撰两书皆成经典之作,可谓学界奇谈。从1938年秋天开始,萧公权在四川峨嵋西郊利用乡间的安静环境,每天晚饭已毕、稍事休息之后,便独坐书斋,走笔于灯下,日复一日。至1940年夏,终于全书杀青,他也偿了怀抱十几年的夙愿。此书印行之时是在1945年,但完稿之日便受到学界同人推崇。此书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极强的原创性和体系性撼动了中国学术界,也惊艳于国际学术界。
1945年抗战胜利后,萧公权又面临着新的难题。这时的交通极为不便,举家北归之路开支浩大,因而他对于是否北上的问题颇感踌躇。他致函清华总务长沈履表示希望若回归清华的话希望能再度入住新南院六号旧居。但可惜此处当时已有人选定,难以如愿。在萧公权看来,这是他的福地。不能重住此地,当然回去的愿望大打折扣。这年6、7月间,他的终生知交、早已在中央位居要津的蒋廷黻又推荐他任上海《申报》主笔,程波沧更嘱其尽速到上海就任。萧公权接着电报时很是高兴,但转念一想,自忖训练、修养、识见、文才都力不能胜,只好致电蒋廷黻辞谢此议,仍旧寻觅教职。
相对于生活尚属安定的堂弟,八哥萧蘧在这些年里的日子就很难过了。抗战爆发后,萧蘧参加抗战政府,在资源委员会工作;但是只做了几个月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彼时的官僚体制。1938年,他从政府辞职,去了云南大学,任庚款讲座教授;1939年,他又回到西南联大任教。奔波之苦自不待言,而此时的联大生活更加艰苦。萧蘧一家租住在昆明城外西山脚下一户当地农民的房子里,屋里房外是泥地泥墙,但院子里可以养鸡。于是,他家里的6个孩子,大概每隔一天能吃一个鸡蛋,每个礼拜能吃一次肉;冬天把窗户用报纸贴了挡风,夜里甚至能听到狼在窗户下面嚎叫。为补贴家用,当年从美国给女儿带回来的洋娃娃也被迫送到昆明典当换钱。他喜穿蓝布大褂,而抗战爆发后的物资短缺,使他的大褂不仅洗得褪色,而且打上了很多补丁,但他照样穿着去讲课。当时的教学参考书很少,萧蘧就把家里的书带到学校去,借给学生阅读。为了节省纸张,他让学生记笔记只记重点,不用记细节。
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课余只好苦中作乐。陈岱孙、李继侗和陈福田常常带着他们的米和二两肉到萧蘧家串门做饭。饭后,几个人就在菜油灯下,一边打桥牌,一边针砭时弊。萧蘧往往直言不讳,批评当局的贪污腐败。有时打牌“三缺一”,他们就教萧的儿子萧庆伦加入其中。生活的捉襟见肘让萧蘧的夫人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为此甚至会和他争吵一番。他夫人有一次抱怨说,是不是应该私下去找梅贻琦校长,先领一点薪水用。但萧蘧拒绝这样做,他说,“大家都很困难。”与很多教授一样,萧蘧也靠做兼职来补贴家用,翻译美国的新闻稿,并给要出国的高级官员做培训。即使如此,萧蘧仍认真教学,从未放松自己,放纵学生。有时他发现学生未到课堂,便会慨然道:“今天我教你们,可是我却没钱给我自己的子女念书,你们还不好念书?”听者无不凛凛,感动异常。萧蘧上课,有板有眼,总会用半小时复习上次的课,因此便有人学会投机,或迟到半小时,或早退半小时,这样仍能接上课业。萧蘧的教学治学态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中有极好的口碑。在离开联大之后,学生们仍对他有深深的追念。
1944年,在陈立夫等人的压力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被迫辞职,学校亟需物色另一位赣人来领导。在赣籍名流吴有训的再三推荐下,萧蘧遂被任命为中正大学校长。他邀请萧公权出任法学院院长,但萧仍本以往的原则而谢绝了。当时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县,日军来袭时,萧蘧组织全校迁向江西的农村和山地继续办学。那时他哮喘很严重,仍然勤奋工作,为学校聘请了一批名流学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正大学复校于南昌,萧蘧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稳定的生活。他积极聘请国外教授回国,并用美国大学的治理方式来治校。但在1947年2月,萧蘧辞去校长一职,再度应聘清华,他把家里的所有行李都运回了清华园。但此时,蒋廷黻又发来邀请,要他到纽约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顾问,为期两年。老友盛情,萧蘧于是辗转前往美国。
萧公权此时的经历也与乃兄相似。清华复员北平,但原先阵容强大的清华政治学系,却遭遇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抗战前的多位教授如浦薛凤、陈之迈、王化成均未返校;原有的骨干教授中,几乎只剩下了张奚若。清华政治学系不得不聘任已在北大任教的王铁崖、吴恩裕等兼职授课,并从武汉大学紧急请来早年的毕业生邵循恪和曾炳钧回校救急。但此时,因各种条件未获满足的萧公权已顿消返回清华任教的念头,仍在成都燕京大学任职教授。但在1946年夏,先有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极力思谋聘请萧公权到北大,后有出任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校长的清华同学兼同事顾毓琇的盛情邀请和周密安排,萧公权终于携家人于1946年8月初由成都飞抵南京就职教授。在政治大学,萧公权同时兼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这在他纯属驾轻就熟,毫不费力,但他仍相当用功,兢兢业业于课业。但这一时期,却又是当局政治崩坏之际,萧公权的生活并不安定,心境亦不甚安宁,除了偶尔做一两首诗以为排遣外,也曾抽暇去凭吊石头城内外的古迹,瞻谒中山陵和谭延闿墓;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雨花台也留下了他的踪迹。但抑郁之情,终难缓解。到南京不久,他作《鹧鸪天》一首:“漂泊西南十载经,游仙枕梦已零星。鬓从三蜀新生白,山在六朝旧处青。”整个社会已开始土崩瓦解,四川出现“抢米”、“吃大户”,南北各地更是物价飞涨,法币五六百万元才买美金一元,大家疯一般地抢购美元黄金,抢不到,就抢购白银囤积起来。
不久,“帝王之都”的金陵也已朝不保夕。就在时局恶化之际,萧公权离宁抵沪,随后应邀赴台湾大学任教。到校时,他得到已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的原清华同事浦薛凤的照料,借住在校长公馆里。清华旧友、考古学家李济到台湾时来探望他,见面笑称:“俨然校长”,萧答曰:“窘哉难民”。1948年春,四川大学转来了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主任戴德华教授的电报,邀请其前往担任客座教授。此时此际,萧公权已回归祖国二十二年却从未踏出国门一步,在当时政局动荡中,他早已为自己的“学业低落”深感痛苦,自然希望去美国看看。但正在办理赴美的过程中,噩耗传来。194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闭幕后,萧蘧从巴黎回到纽约,途中受了风寒,哮喘因感冒恶化,治疗中又遭逢医疗事故,因而不幸去世。萧公权悲痛逾常。“哥俩好”的故事,业已曲终。
翌年9月,他向台大告假一年,登上“中国熊”邮轮驶往旧金山。在华盛顿大学,他遇到了他的清华校友李方桂等人。而几乎在此同时,在风雨飘摇的南京,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出,萧公权以其杰出的成绩当选为院士,他是极少数完全依靠学术成就(而非管理工作)当选为院士者之一,也是政治学仅有的两位院士之一(另一位是他的清华同学同事钱端升)。但在此时,萧公权已再次立足于美国学术界。
归途原来是异乡
将离别台大之际,萧公权原无久居美国之意,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而且一儿两女已在台大肄业,他更考虑到要让子女到美国继续深造,于是,他向台大提出辞职,在华盛顿大学的临时教职也改为终身教职。与蒋廷黻一样,原本“暂居”美国的计划,终于变成长住他乡、并最终叶落异国了。
但正是在美国,萧公权很快被公认中国学研究界屈指可数的巨擘之一,进而又为矫正美国的“中国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一批学人的努力之下,西方汉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旧大陆移到了北美新大陆。在华盛顿大学,资料的欠缺曾明显制约了他的研究工作,他不得不为改善这种状况付出巨大的努力。

到1953年秋,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工作大体上完成后,他开始草写《中国乡村》一书。每章初稿写成后,他就会印制复本,送交“中国近代史讨论会”(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lloquium),请同人提出意见。1955年秋,萧公权终于完成这部“开荒”性质的著作,这不仅意味着萧在中国思想史上已达到世界级水准,而且标志着他在中国社会史方面亦已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此书问世之后,好评如潮。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当年即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和奖金1万美元颁授萧公权。萧公权在接获这一通知时,却颇感意外。在获奖的十人中,有史家六人,他受奖理由是“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这项奖赠给你,是为了承认你的崇高学人地位,并且为了承认你在人文学术上的卓越贡献。”这大概是华人首次在美国问鼎此一殊荣。一时间,国内外的亲友都向其道贺,甚至一些素不相识的美国人士也向其表示庆贺。盛名之下,该书很快便告售罄而不得不很快加印。人类学名家施坚雅申言,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方可信而有征地分析中国,进而作各种“跨越文化的尝试”。还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作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
后来,在《中国乡村》一书所作研究的基础上,牟复礼(F.W.Mote)和郎玛琪(Margery Lang)帮助83岁高龄的萧公权整理出版了《帝制中国的和解》。此后,由于康有为次女康同璧的帮助,他又见到了康有为许多已刊和未刊的著作摄影胶片,这成为他第二个研究课题。之后他投入《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的写作之中,利用大批康氏未刊资料,深入探微,论析精当,颇能发覆钩玄,成一家言。该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于1975年印行。几年后,他又出版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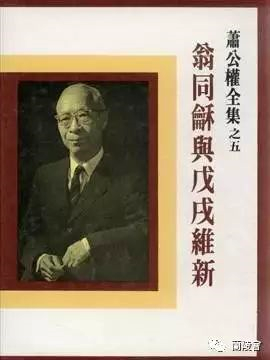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年逾七十的萧公权,在他所任教的第十二所大学——华盛顿大学——也要退休了。他在春季学期讲授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学生知道他即将退休,争着来选修这课。一大间教室挤满了人,来的迟一些的人,往往没有座位,干脆就站在墙边或席地而坐。
那年的5月31日,时届期末,他即将中止自己连续42年不曾中断的教学生涯。下课铃响,当他要走下讲台的时候,坐着的学生一起起立,鼓掌致意。在当时美国教师尊严日趋衰降的时候,他能得着这样的礼遇,殊为难得,更使他相信在华盛顿大学的十九年光阴不曾虚掷。他在走出教室之前对这些学生说:“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珊达雅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只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I hava a date with spring ),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着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是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罢。”
萧公权退休后,蛰居一隅。宅门前翠竹繁花,时有鸿儒来往。长期的海外生活,已让他渐感适应。但牵念所在,仍是故园的古道西风。纵或在欢娱之际,他仍难掩故国之思,惟以“亡国大夫”自称。
“天意从来高难问,道高犹许后生闻”。所幸在华盛顿大学,他有了一位从宝岛飘洋而来的弟子汪荣祖。汪荣祖之于萧公权,一如唐德刚之于胡适之。有着这位晚辈,这位长者多少能减几分暮年的怅惘;后人对这位精博无涯的宗师,也多少能增几分“了解之同情”。只是,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终究还是在西雅图遽归道山,没能与其堂兄在一起,也未能重返故国。1981年11月4日,萧公权逝世于美国西雅图,终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