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沈从文,人们总是会想起他的故乡凤凰,会想起他笔下的“边城”。其实,单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其实也非常密切,86年的生命中,沈从文有49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住在北京。他在胡同里生活,在胡同里写作。北京见证了沈从文一生的起起伏伏、苦辣酸甜,更见证了沈从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的人生传奇。沿着沈从文的生活轨迹重走北京,不禁让人感慨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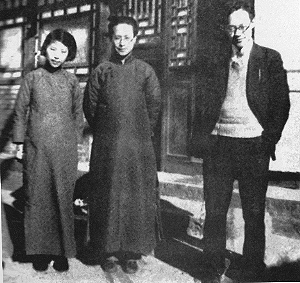
巴金(右一)拜访沈从文夫妇
从“边城”到京城
每年,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慕名到湖南凤凰去,为着是寻访沈从文的“边城”。而在1934年,沈从文去乡18年、重返湘西之际却悲哀地发现家乡处处显出社会变革的痕迹,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事实上,“湘西世界”的美好更在于文学表现当中的人情美、人性美。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西”也只是存在于想象和追忆当中吧——现实中沈从文“凤凰话也不会说”,“完全是四川腔”。
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之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三天之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

位于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是1923年沈从文到北京后的第一处住所 冯雷摄
西河沿街原来位于前门护城河的南岸,站在胡同里朝东望去,巍峨的正阳门依然遥遥可见。想当初这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清末民初时,西河沿街是北京的“金融街”,许多银行、证券交易所都集中在这里。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戏楼历经三百年沧桑却屹立不倒,里面的纯木结构戏楼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能保存下来实在是幸事。向东出了西河沿街,沿着煤市街往南走,经过几个路口右手边就是杨梅竹斜街了。
我第一次去杨梅竹斜街的时候是2011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空横拉竖拽的电线,街道上显得杂乱无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七家书局,据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都经常到这里来。胡同里的青云阁是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一时风光无二。2017年初春,我再去杨梅竹斜街的时候,发现胡同已经修葺一新,路面平整而干净,如蛛网一般的电线都没了踪影。胡同两侧还清理出许多名人故居和商号旧址,真好似是从时光的河流里打捞出来的一样。胡同深处路北的61号院就是当年的酉西会馆。据沈从文描述,“会馆约大小二十个房间,除了经常住些湘西十三县在京任职低级公务员之外,总有一半空着”。我曾走进院子里去,里面的通道只容得下两个人错身,角落里还有不知哪一年的枯枝落叶,我拐了四个弯一直走到院子的尽头,然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当年的会馆现在已经变成普通的大杂院了。
会馆是明清时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北京文学地图”的重要内容。会馆大多集中在宣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外地考生由陆路进京必过广安门,由于内城不许汉人居住,所以进城后大多就近在宣武门附近落脚休息。这里距考场贡院不算远,而且又临近大栅栏、琉璃厂和东骡马市大街,繁华热闹,应有尽有,生活条件便利。极盛时,全北京的会馆有将近400多所,足可见规模之庞大。现在能找得到的还有绍兴会馆、湖南会馆、湖广会馆等。2012年夏天,我还曾去过康有为住过的广东南海会馆,可2016年再去的时候,周围已经被蓝色的施工围挡圈起来,里面什么都找不到了,手机导航显示“该地点已关闭或搬迁”。实在是可惜。
不难想象,会馆里虽然凡事都有个照料,但周围毕竟都是同乡,而非志趣相投的同道。所以转过年来,沈从文又搬到了沙滩附近的公寓里,这里离北大更近,周围有好多和沈从文一样的年轻学生,沈从文陆续认识了刘梦苇、冯至、蹇先艾、胡也频、丁玲等一大帮年轻人。沈从文的住所名为公寓房间,实际上是由储煤间临时开窗改造而成,“既湿且霉”“尽可容膝安身”,沈从文名之为“窄而霉小斋”。这个名字随着沈从文迁徙而沿用,直到他“文革”后搬进楼房里为止。这段时间沈从文写了大量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从中不难看出他饱受“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双重夹击,生活非常不容易。这样的光景,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动摇过,1924年他曾想过回家,或是到北方去当兵,再或去学照相。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时时想起他初来北京时姐夫田真逸对他的鼓励“可千万别忘了信仰”。来北京这是沈从文自己的选择,坚守下来也可谓“不忘初心”吧。
透过沈从文的选择和坚守还应当意识到的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阶层流动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沈从文自己也曾说“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即在地方凭借宗族关系和家庭威望作几任小官,娶妻生子。然而早年的行伍生涯中让沈从文看饱、看厌了杀戮,再加之生活中一系列偶然事件以及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这些促使沈从文思考生命的意义,最终决定挣脱命运的公式,做一个“自由人”“独立人”,“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这似乎是时代的共识。青年鲁迅惶惶然却还是选择“走异路,逃异地”。胡适在赶考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途中致信母亲说“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同样,沈从文也是抱着做“学生”的梦想来北京的。如果说“学生”这样的身份似乎铺就了觐见“德先生”“赛先生”的未来之路,那么“北京”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且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符号,是一种被赋魅的政治承诺和文化承诺。“北京”是历史造就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她意味着文明与新变,意味着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进步,这种想象时至今天也依然如此。而这恐怕也是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

沈从文暂住过的银闸胡同 冯雷摄
现在,在北大红楼附近的银闸胡同、北河沿里,当年的公寓早已无影无踪了。不过这里每天仍然熙熙攘攘,全都是参观故宫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游客,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那些不起眼的胡同里,曾有许许多多像沈从文一样的年轻人在苦熬、织梦吧。
达子营28号院:传奇的巅峰
1928年1月,沈从文随着南移的出版业而一起迁居上海、武汉,此间曾短暂地回京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师宿舍,几个月后应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直到1933年七八月间,沈从文又重回北平。他先是暂住在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振声家里,紧接着很快就付定买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
“府右街”明朝时叫“灰厂夹道”,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将总统府设在中南海,以总统府为中心面南背北,灰厂夹道恰好在总统府的西侧,即右手边,因此名为“府右街”。“达子”即“鞑子”,是当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贬称,民国政府倡导五族共和,改称“达子营”。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1年要求“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北京市根据这一指示重新命名了许多地名,其中西安门府右街的达子营改名为“互助巷”。2012年,我曾去找过一趟“互助巷”,最终却什么都没有找到,拆迁过后周围都是普通民居和政府办公机构,让人觉得有些许的遗憾。
沈从文在达子营28号院住了4年,这4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为安定、顺遂的一段时光。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张兆和,成就了一段佳话。更有意义的是,28号院还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新婚之后,沈从文接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他的家成了北平重要的文学据点。不久,好友巴金从上海赶来看望沈从文夫妇,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腾给巴金住,住在沈家的两三个月里,巴金写完了《爱情三部曲》中的《雷》以及《电》的一部分。而沈从文则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交叉写完了《边城》和《记丁玲女士》,达子营28号院见证了沈从文创作巅峰期的到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3、1934年间,沈从文在这里完成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一系列文章,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大幕,最终连鲁迅也介入到这场论战中来。
沈从文批评上海文坛商业竞卖包装下的“名士才情”和“玩票白相气息”,肯定北方作者的“诚朴治学的风气”及其对“人生文学”的关注。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连同他关于“都市—湘西”风格、情感迥异的两套笔墨共同奠定了沈从文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经过一辈辈学人的分析和阐释,提及“京派”与“海派”必定绕不过沈从文,而讨论沈从文又一定会提到他笔下的城乡二元世界,这已经成为文学史的结论。但有趣的是,如果说在观念上,沈从文贬抑都市文明的“下流”“虚伪”“愚昧”“残忍”“丑恶”,可在现实生活中,跻身于教授名流之中却一直是沈从文孜孜以求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位教授。”丁玲这番话虽然说得有些不讲情面,但事实却也的确如此。如果说沈从文推崇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美,可是《柏子》《萧萧》《丈夫》《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等当中的嫖妓、童养媳、沉潭、盗墓、奸尸等,无论如何都是有违公序良俗、天理人伦的,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都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与批评。如果说沈从文只是对上海没有好感的话,可他许多嘲讽都市人的小说比如《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等却又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1931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沈从文又一再表示北京于自己不相宜,还是上海更适合自己。如此说来,文学史书写或许草草掩盖了不少矛盾的地方。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之前,沈从文的生活极其艰难,他对都市文明的鄙夷和批评综合了他在许多城市生活的经验。《或人的太太》和《焕乎先生》分别发表于1928年3月和5月,此时沈从文尚在北京,故事的背景都涉及北京,后者部分涉及上海;《绅士的太太》发表于1930年,沈从文已到上海,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做官人家”的种种不堪;《都市—妇人》发表于1932年,此时沈从文人在青岛,小说背景在武汉、北京、上海之间不断切换;1935年发表《八骏图》的时候,沈从文已经在北京达子营的家中安定下来,主人公周达士的小病非在青岛不能痊愈。可见,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攻讦并不针对特定的城市,而是源自于他对现代文明负面效应的抽象总结。而且,沈从文心里也清楚,人生前路的方向绝不在湘西而在城市。且不说他自己对胡适、徐志摩等文坛大佬的干谒和结交,他自己曾雄心勃勃地想要学习外语,甚至还想把自己的九妹送到国外去,而且是“学一些读书以外的技能,学跳舞或别的东西”。而谈到湘西题材的创作,沈从文曾不无沮丧地谈到“我的世界总仍是《龙珠》《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沈从文抑“城”而扬“乡”,这一创作特色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他渴望融入城市而不得的一种心理焦虑及补偿呢?而学界把这种特色提炼、概括为“城乡二元对立”,这是否又和特定语境下我们对乡土文学传统的重视与维护有关,也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体现呢?其后人们对“反思现代性”的想象和追求,是不是又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对这一结论的接受与维护呢?
达子营28号院是沈从文的福地,短短四年时间里,《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沫沫集》等一批重要作品相继问世,除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外,沈从文还参与发起了《水星》和《文学杂志》等,并被林语堂聘为《人间世》的特约撰稿人,沈从文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沈从文还晋升为两个儿子的父亲。然而战争却打断了原本顺畅、美妙的生活节奏。1937年7月18日左右,沈从文躲进德胜门内的国祥胡同的那王府后院暂避兵燹。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11日晚,沈从文接到民国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第二天一早随北大、清华的教师匆匆撤离了北平。
涩重而辉煌的传奇终篇
抗战胜利后,伴随着西南联大的解散和回迁,沈从文于1946年8月27日返回北平,开始了“后半生”的生活。
返回北平后,沈从文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辅仁大学兼课。年底,沈从文搬进沙滩中老胡同的北京大学宿舍居住。中老胡同和西老胡同连成一个九十度的拐弯,中老胡同东口正对着北大红楼,西老胡同的北口正冲着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当初沈从文和朱光潜、冯至、闻家驷、马大猷等三十多位一起住在32号院。院子原是光绪的瑾妃买给娘家的,“三个三层的四合院,花园、假山和一百多间青砖瓦舍,在北平沦陷期间统统被日军霸占。从抗战胜利的1946年到院系调整的1952年间,这里是老北大的宿舍区之一”。今年年初我曾去过一趟中老胡同,发现那里变化很大,都是小宅门的民居,现在的32号院想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宿儒聚集的宿舍了。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初,沈从文被安排到鼓楼附近的拈花寺,参加了十个月的政治学习,东面不远处恰好是他当年曾经短暂住过的国祥胡同。以往,或许是出于对极“左”思潮的清算,或许是出于对沈从文的喜爱与同情,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沈从文后半生不得志的一面,但实际上,沈从文不但顺利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文代会,并且在1956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周扬还曾邀请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被沈从文拒绝了。可以说“文革”爆发以前,文坛高层对沈从文还是比较客气的。至于说40年代末沈从文精神失常,除了政治压力外,也和他家庭内部矛盾相关。无视这些,恐怕既不利于认识复杂的历史语境,也不利于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沈从文。
当然,在生活、工作方面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这也是事实。1952年,在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家被迫迁出中老胡同搬到北新桥附近的交道口大头条胡同暂住。1953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得了三间房子的宿舍,房子面积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睡觉都难得安定,尤其房子与院子里的男女厕所相邻,均为茅坑式,沈从文自嘲住处是“二茅轩”。虽然条件较差,但总算有了安定住处。可“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又强迫沈从文腾出两间房。1969年秋冬之际,沈从文夫妇拖着病老之躯先后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到1972年2月返回北京后发现,那间唯一的“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小房子也被别人占用了。同年夏天,作协看情况实在太过艰难,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间房,约十九平方米,距离东堂子胡同宿舍约两里地。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在东边的小羊宜宾胡同,沈从文每日中午赶来吃饭,然后再带上两顿饭,穿过赵堂子胡同返回西边的东堂子胡同。这样食在东边住在西边成了他每天的规定动作。1978年3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在胡乔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1980年,沈从文终于分得并勉强接受了一套并不理想的小三居,就在新侨饭店背后,房子在五楼,因为临街,噪音很大,沈从文夫妇常感到精神疲惫。这几处我也都去看过,胡同还在,但房子似乎已经都拆掉了,当年的景物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存有蔡元培故居,胡同中段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去往小羊宜宾胡同要经过赵堂子胡同,胡同深处存有朱启钤故居,现已沦为民居;再往东不远处就是赵家楼饭店,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这里,附近路边还有一座“火烧赵家楼纪念碑”,碑文由沈鹏撰写,只是纪念碑实在太不起眼,若非专门去找,恐怕没有谁会注意的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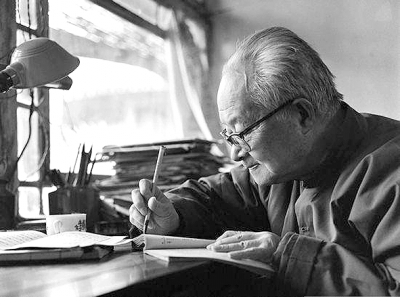
晚年的沈从文
仅就个人居住条件而言,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确有些动荡、狼狈。1980年初搬进新家之前,沈从文还曾给巴金写信,描述他和张兆和轮流用一张桌子的情形,“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在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而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沈从文的生活遭遇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辈作家中能取得类似成就的却几乎无出其右。通常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是他文物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小部分。1974年他曾向领导汇报自己已经“拿下”的领域,包括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等等。如此环境如此成果,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全集》,皇皇32卷,其中有5卷是物质文化史研究。沈从文胡同传奇的终篇虽然涩重却也足够辉煌,让人深受震撼与鼓舞。或许这正是“传奇”的本色吧。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北京城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