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余冠英,中国古典文学专家。1906年5月16日生于江苏扬州,1995年9月2日卒于北京。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任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1926年,余冠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他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喜欢创作新诗。四年级时,冠英在同学中组织了“唧唧诗社”,每作一诗,社友们都要评头品足,在相互切磋之中体味诗之欢乐。
除诗之外,冠英的小品、散文、小说也很出色。他用汉朝大将“灌婴”之谐音为笔名,大多发表在《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上。这些文章有的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当代散文精华》收入,有的被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入。同时代的吴组湘教授在1931年写的《清华的文风》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余冠英当时的作品,称余冠英是清华的代表作家,代表了清华的文风……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冠英编辑影响很大的《国文月刊》到40期。
1938年5月,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暑假后,又从蒙自迁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后,带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赶往昆明,出任联大师范学院讲师,后又擢升副教授、教授。1945年后,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教授被害案相继发生,法西斯的独裁行径使冠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多次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1948年6月18日,他与朱自清、金岳霖、吴晗、陈梦家、钱伟长、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即《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
1952年院系调整后,余冠英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余冠英成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改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
此文为余冠英先生外孙女婿刘新风在商务印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合作举办的“百年学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刘新风曾任教于东北师大、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余冠英
余冠英先生曾经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文学史家,我至多就是对上古文学,尤其是对先秦至于汉魏六朝诗歌略知一二,不敢说是一个文学史家”。其实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一点也不为过。而且,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
简单地说,余冠英一生做了几件事。一是教书,一是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作编辑工作。一直到晚年,将近8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做《文学遗产》的主编。
余冠英的三重身份与学术成就
首先,他是著名学府的一位大学教授。
余冠英在抗战爆发之初,西南联合大学肇始的时候,就成为了副教授,而在抗战结束之前,便已经晋升为教授。从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复校回到北京,一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他一直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授课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诗和中国文学史。
《汉魏六朝诗论丛》应该是余先生的成名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际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创作于这个时期以前。当时余先生年富力强,虽然国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他个人家庭负累也比较重,但是他仍能一边教书,一边做大量编辑工作,并挤出业余时间搞自己的专业研究。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文科全部被砍掉了,中文系也基本上被合并到北京大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余先生就和俞平伯先生、钱锺书先生等人一起到了文学所。再后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被划拨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变成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文革”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现在建国门西北角的大楼,随即“文学所”又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先生从一开始做文学所古代文学组组长,后来又做了文学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再后来还兼任《文学遗产》主编。
其次,他是一位最高学术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随着工作单位的变更,余先生的第二重身份,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以后,他不是以教学为主了,而是以学术研究为主,专门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和古籍整理规划的确认、协调、组织与实施。他在做文学所的领导、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顾问的漫长时间里,还要承担很多科研任务,完成很多个人或者集体的研究项目,带博士研究生,一直做到退休。最后,到80来岁,身体和精力都不行了,他才退下来。
他在文学所刚刚成立的时候,就被确认为二级研究员,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情况特殊,学术职称评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他的职称也就一直没有变动,直到退休。当时,文学所只有两位一级研究员,一位是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是同学,算是胡适的学生,也是余先生的老师)。还有一位就是何其芳,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何其芳的资历和年龄都比余先生晚些,他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之后,就去南开附中当了老师。1938年,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第三,余先生在做教授和研究员之外,还有一项很少有人提到的工作,就是他兢兢业业地做了一辈子编辑。当然,做编辑是兼职,不是他的主业。他年轻时刚入清华,就接手编辑《清华周刊》。“清华”有个传统,就是由前后期的学生们接续着做《清华周刊》的编辑。余先生曾在回忆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说朱自清先生也写一些古诗、小词,风格近“花间体”,所以朱先生从来不拿出来示人,但是他和余先生关系非常要好,所以一次拿给余先生看。
余先生看了觉得不错,提议发表。朱先生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在余先生的劝说下同意发表了,但却说什么也不同意署自己的真名。所以余先生只好选了一些,用假名字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这个时期(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余先生开始进行新文学创作,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并且陆续在一些杂志、报纸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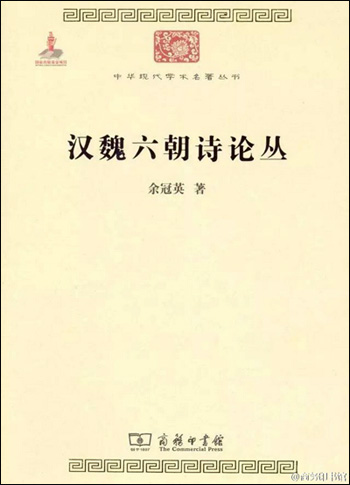
关于他的新诗创作,学术界近些年有一种新的说法(这是在余先生去世之后才被提出来的,因此已经无法和他本人探讨、核实了):有人专门写文章,把他作为新月派后进的作家之一,进行研究。为什么呢?我认为因为现在所谓新月派的作家、诗人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这可能是他被划归新月派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写的诗也近乎新格律体,他受闻一多的影响很大。闻一多是清华的,朱湘是清华的,曹葆华是清华的,饶孟侃、杨子惠、陈梦家这些人,都是清华园有名的诗人,而且多多少少都和余先生有些交集、交往。曹葆华和余先生是同学,三四年级他们就在余先生的组织下成立了“唧唧”诗社,一起写诗,一直有很深的联系和来往。
抗战期间,余先生受朱自清先生委托,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他前后做了五年的《国文月刊》编辑,可以说是独立支撑了大后方一个难得的纯粹的学术殿堂,因而,他的付出,也广受学术同行们的赞誉。后来,在建国后,他先是被点名做了《光明日报》学术版“文学遗产”的主编,后又主持文学所主办的《文学遗产》杂志编务数十年,可谓筚路蓝缕、任劳任怨,无论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尽可能地既洁身自好又超凡脱俗,打下了这个国家级古典文学研究堡垒的坚实学术根基。
余先生是扬州人。崛起于清代的扬州学派是典型的选学派。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背景,可以产生不同的学术流派。余先生是扬州学派的传人,受前辈乡贤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学术研究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清代的朴学和传统的汉学思想的影响的,因此大家在读余先生学术著作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他读书之博与精到细致。他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注释,虽然有很多东西不去署名,不去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强调这个东西是哪来的、那个东西是哪来的,但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因为他总是通过不同作者的不同释法,总结提炼出一个最可信的、选择一个最好的解释,贡献给读者。所以,看起来一个简单的普及性读物的背后,有着很强大的学术功底。
在学术上,他的主要成就一个是对“诗经”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文人诗进行选辑、注释的工作,第二是对部分“诗经”进行白话文翻译。此外,他参与组织、主持了几个重要的集体项目的编写工作。其中主要就是两个,一是文学所的古代文学组主要精干力量(包括钱锺书先生)全部参与编选、注释的《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余先生为主编,从体例、选目到任务分配,到注释、修改,直至最后通稿、审稿都是余先生亲自主持、完成的。这个项目做了十八年,从1962年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才正式出版。还有一个,就是在1962年出版的社科院版的《中国文学史》。余先生是这套书的主编。
这部著作分三段:隋之前的,由余先生自己作分段主编;唐宋一段,由钱锺书先生作为主编;最后一段,元明清以后这段,由范宁先生作主编。(范宁先生当年与季镇淮先生一起读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是闻一多先生亲自带出来的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曾和闻先生一起写文章,学术功底相当深厚。)最后,由余先生统稿。余先生在这项工作中付出精力最多、出力最大的,就是牵头并且参与创立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架构,然后组织力量编写、起草,直至通稿、成书。初创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构架这一点,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很简单,但是在建国之初,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是筚路蓝缕阶段,前面没有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模板可供参考,所以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但是,起码可以说余先生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并不为过。看余先生的成就,一定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动态地触摸和理解,体味一个立体的完整形象。

余冠英夫妇
余冠英的朋友圈
说到余先生朋友圈,我现在大概区分一下,其实有很多是区别不开的,因此不一定科学。
第一类就是“朋友”(很狭义的)。和余先生有君子之交的,朱自清是最密切的一个。余先生在1926年下半年就加入共产党了。他还介绍了同宿舍一个叫朱理治的经济系学生入党。朱理治是1907年生人,比他小一岁,晚一届。“四·一二”的时候,北京的军阀抓共产党,风声很紧。余冠英和朱理治的左派倾向很明显,当时很危险。余先生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带着朱理治藏在朱自清先生家里,躲了一宿,第二天两个人才分手。这说明朱自清先生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们俩是共产党了,但是在风声那么紧的情况下,朱先生还是仗义施以援手,说明他们的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他的“朋友”,如果说有第二个,那就是吴组缃。余先生和吴组缃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一开始吴组缃的哥哥和余冠英是同学,两个人挺好。后来吴组缃又考过来了,他考的是经济系,第二年转到文学系,两个人通过他哥哥认识,很谈得来,交往也就越来越深了。
第二类是老师或老师辈的。余先生的老师辈、跟他也有很多交往的,比如说俞平伯先生。两人在一个组,一直在一起工作,余先生是组长,俞平伯是组员,可谓订交一生、不离不弃。还有一位,闻一多先生。他长期做清华或者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主任。有一件事,当年萧涤非先生在四川大学教书,因为国民党要让他加入国民党,他不愿意,结果被国民党找茬解聘了。萧涤非先生孩子多,全家被困在四川,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写信给余先生,请余先生帮忙,想去西南联大教书,甚至说如果大学没有位置,教附中也行,只要孩子们不挨着饿就可以了。余先生当时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他拿着萧先生的信找到闻先生求情,闻先生不太了解萧先生,就问萧先生学问怎么样。余先生说,他是我大学同学,同一届,而且都在清华足球队一起踢足球,交往很多,学问也非常好,所以我可以打保票。闻先生说,我信你,于是便给萧先生安排了一个教职,在中文系教书。可见,闻一多先生对余冠英先生还是非常信任的。
闻先生孩子多,抗战期间生活困难,一度要靠给别人刻印章挣点钱以补贴家用。余先生当年家里人口少,情况要好些,所以曾经为了帮助闻先生,也按照闻先生刻章的润格,请他帮忙刻了一方闲章。可惜这枚印章在“文革”时被抄走,丢了。余先生曾经对我说:很可惜,那是闻一多先生留给他的唯一纪念。1946年夏,闻先生遇害以后,在朱自清先生主持下,清华大学成立《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余先生责无旁贷,做了四个具体做工作的编辑之一,不但要投入很多精力积极参加当时的民主运动,而且不惧风险,从始至终参与了闻先生的后事料理,还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到对闻一多先生遗稿中唐诗研究部分的整理之中了。《闻一多全集》之所以能够很快结集出版,当然也浸润着余先生的很多心血。
第三类是“同学”。其中有一位叫郝御风先生,他是余先生晚年经常念叨的几个好同学之一,他后来是西北大学的教授,但是专业不是古典文学。上学的时候他和余先生是好朋友,也是“唧唧”诗社的成员,后来搞文艺理论、文艺学了。每一次他来北京,或者是余先生去西安,两个人都要见上一面,一起把酒言欢、回忆彼此的青涩年华。
还有一位叫张骏祥,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张骏祥是我国著名导演,是电影界的才子,曾经当过上海电影局的局长。
第四类呢,我也想了半天,怎么归纳,后来我就权且这么说吧,叫“同好”。这里边有的算是同学,有的算师弟或者师兄,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浦江清,一个是李嘉言,一个是许惟遹。这三位都是教授,而且都是英年早逝,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去世了。这三个人和余先生是当年很谈得来的朋友,浦江清和李嘉言都是研究汉魏六朝的。浦江清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学问很好。
第五类算是师弟,就是比他小几届,大概都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个阶段入学、或者毕业的,王瑶、季镇淮、范宁,何善周、曹禺、钱锺书、李长之、林庚,包括季镇淮,这些人进清华都比他晚了。王瑶先生三十年代,也就是在抗战爆发前,就考了朱先生的研究生。我曾经去王瑶家拜访他,我跟外公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个条子,我去王先生家不让我见怎么办,他说你就去,就说我让你去的就行了,并且告诉我王家住在哪儿。我去到王先生府上,夫人出来了,问我是谁。我说是余先生让我来的,他让我来找王先生。王师母就马上进去了,很快王瑶先生便走出来,和我聊。我说,我现在搞现代文学,想来跟您请教,学习啊。王先生就说,你搞新文学,去问你外公啊,他比我还熟。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外公曾经搞过现代文学,搞过新文学,王瑶先生跟我亲口说,他说我最初搞新文学,第一批资料是你外公给我的。他毕业之后,兴趣转向了,去搞中古文学。我那个时候是跟朱自清先生学中国文学的。但是我对新文学感兴趣了,余先生就把他当年买的所有的文集、诗集,他订的所有的杂志,全部一股脑地都送给了我。所以,王瑶先生随即客气地说:“我研究新文学还是跟你外公学的呢”。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当不得真,但是这说明俩个人当年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后来他们因为年事都高了,又不是搞一个专业的,所以交集也就越来越少。有一次,我陪余先生去吴组缃先生家做客,如果不是聊了一上午,已经很累了,说不定他和王瑶先生这两位老友也能见上一面呢。
季镇淮、范宁都是闻先生的研究生,何善周当年是闻先生的助手,助教。曹禺、钱锺书、李长之他们三个,大家都熟悉,就不用说了。钱、李二人,加上林庚、吴组缃,即所谓“清华四剑客”。但是他们比余先生晚,钱、吴和林庚应该是33届的,李长之更晚。余先生1931年毕业。
第六类,我把他们单列是因为关系特别。这几位都是他的领导,但是叫领导又不完全合适,所以我把他归为“师友”吧——一个是郑振铎,第二个是何其芳,第三个是沙汀。余先生和这三位在工作上接触很多,所以彼此交往也就不少。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去何其芳家里,去讨论问题,大概就是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那段时间。后来注释“不怕鬼的故事”,就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一位中央领导说,咱们搞一个不怕鬼的故事,毛主席就是不怕鬼嘛,是不是?所以文学所在何其芳先生的领导下,很快就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那个小册子虽然很薄,但是集中了文学所很多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
第七类,我把他叫“同事”了。其实主要是两个时期的同事,一个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这一段,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他在文学所的这一段。早期那一段有王力、陈梦家这些人。尤其是陈梦家,他们两个都爱写诗,他对陈梦家也很推崇。陈梦家相对很年轻,年纪小,但是写的诗和后来他研究文字学,学问做的也好。他们交往比较多些。后来在文学所,同事就多了,这里面有长辈的,比如说王伯祥、孙楷第,比他年纪大;蔡仪、吴世昌和他年纪差不多,还有吴晓铃、唐弢,比他年轻几岁。另外,还有陈友琴和陈翔鹤,年纪也比余先生稍微大一点。
第八类应该叫“学友”。其实,周振甫先生应该是这类的,但是因为晚年和他走的比较频繁,我就规到朋友那一类了。学友里面有程千帆先生,王运熙先生,包括比他年轻的,像陈贻焮先生,廖仲安先生、徐放先生、林东海先生、李华先生。这些人和他联系都很多,互相之间有交流。本来,陈贻焮先生和廖仲安先生,尤其是李华先生都是执弟子礼的,一定要叫余先生为老师,但是余先生却把他们作为朋友,走的也比较近。程千帆先生是非常尊重余冠英先生的,他经常给余先生写信,几乎每次写诗都会寄来,手书,请余先生指教。王运熙先生非常内敛,性格似乎不太外向,学问做的非常扎实,是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也搞汉魏六朝,他每次有新书出版,都认真地寄送给余先生,公公正正地向余先生请益。他到北京来,都到家里来看余先生,两个人虽然话不多,但是那种高层次的交流,我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还有一类,第九类,就是有点亲戚关系的。比如说来往较多的有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比他晚,是陈含光先生的外甥,就是余先生大舅哥的外甥,论起来还比他晚一辈。还有一位就是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原来,卞孝萱先生和余先生到底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始终搞不明白。后来卞孝萱有一个小短文,我一看明白了。卞先生在文章里说的非常简单明了,他说:余先生是陈重庆先生的女婿,陈重庆是卞家的女婿。等于说是余先生的岳母姓卞,就是这种姻亲关系。卞孝萱先生早年来过余家,后来在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偶尔和大舅余绳武先生碰上,便在一起叙叙旧。赵朴初先生有一段时间——就是“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到余家来拜年的。
还有一类,从共产党的角度说,就是同志了。有两个接触较多的人,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朱理治。朱理治不说了,胡乔木是什么关系呢?胡乔木的哥哥也是余冠英的同学,后来通过他,胡乔木便认识了余先生。1949年以后,因为胡乔木一直是这方面的一个领导人之一,所以和余先生又建立了联系。
最后一类,那就是他的学生了。

余冠英全家福
我所知道的余冠英先生
余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家里面请安,陪他一起聊聊天。他的大儿子余绳武,是搞近代史的,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自己的工作任务也很重,主编过《沙俄侵华史》四大卷。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从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就开始筹备、编写,一直是由余绳武先生主持。他们父子除了吃饭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基本上是各作各的学问。我虽然在古典文学方面差得很远,但是对于现代文学领域里、也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还算略知一二,他熟悉的人我也基本都知道,所以还可以经常陪他聊聊天。
我对余先生是非常崇敬的,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崇敬他,而只是作为一位和蔼的长辈那种简单的崇敬和崇拜。作为学者,我觉得余先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位老人,他不张扬,不卖弄,朴实无华,作风严谨,自持内敛,人格高尚,确实是一辈子追求的就是淡泊。晚年因为得了糖尿病,年纪也大了,家里对他吃的东西,看的很严。
他爱吃零食,和朱自清先生一样,有的时候就自己拎着拐杖出去了,到家附近的小卖部买一点雪糕、饼干之类的零食吃,回来时还得揣在口袋里藏起来。老先生有他的可爱可敬的一面,但是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他晚年腿脚不利落了,家在昌运宫社科院宿舍住,去马路对面的紫竹院散步都很困难,得坐着轮椅去。有一年——究竟是哪年我忘了,我们下定决心推着他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他一路上显得十分兴奋,因为有多少年都没来过了。
还有一次,我陪他专门去吴组缃先生家,吴先生也是高兴得不得了,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临别时,吴先生送我们到门口,两个人又站在门口继续聊,聊了半天,总说走吧,中午了,该吃饭了,眼看着就快到下午一点了,可还是恋恋不舍……最后,吴组缃先生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下楼,说:见一面少一面了。这对老朋友,那次果然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吴先生就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看他们老哥俩坐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谈天说地,那个默契,那个开心,那种你有上句、我有下句的感觉,就仿佛重新回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下就年轻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