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著名学者、诗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为正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读书的一个大学生编写的歌谣集《西南采风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序文。这个大学生就是我的父亲刘兆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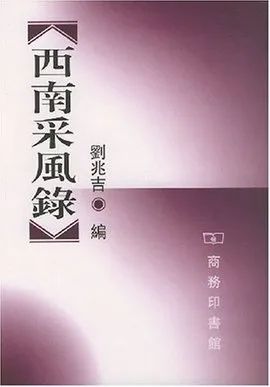
《西南采风录》书影
整篇序文慷慨激昂,正义凛然,饱含忧国忧民之情。但其中有一句话,“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不是很理解。全篇序言似乎都是在回答“你说”的观点。我想,既然这篇序文是闻一多先生为父亲的歌谣集所作,那么,序文中的“你说”应与父亲多少有些瓜葛。
一次,我鼓起勇气问父亲:“闻一多先生的这个‘你说’指的是什么?”父亲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稍稍踌躇了一下,就微笑着点点头,同我讲起当年在湘黔滇步行团步行途中,闻一多先生和这本歌谣集的故事。
壹
1938年初,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几百名师生组成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跋山涉水行进在湘黔滇崎岖的山路上。我的父亲刘兆吉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三年级学生,也在步行团中。沿途,他注意采集山歌民谣。一日,刘兆吉兴冲冲地把刚采集到的几首歌谣拿给闻一多先生看。这几首歌谣的内容让他有些困惑,其中有两首是: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
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
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把火烧。
闻先生看过后,很感兴趣,反复吟诵,赞不绝口。刘兆吉见闻先生对这几首歌谣如此欣赏,很不理解,问道:“这不是在歌颂土匪强盗吗?多么原始,多么野蛮,有什么好的呢?”

闻一多先生
谁知刘兆吉的话一下惹怒了闻先生,他突然发起火来:“密斯特刘,你脑子一点也没开窍!”
刘兆吉一头雾水,不明白老师为什么突然发那么大的火,因为他觉得自己对那几首歌谣的理解并没有错。
一年后,刘兆吉把他从长沙到昆明步行3500余里、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集的2000多首歌谣汇精选出一些,编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出版前他请闻先生写序,闻先生欣然同意。显然闻先生并没有忘记一年前他与刘兆吉在湘黔滇步行途中的那场争论,所以他在序中对刘兆吉的疑问给予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读着闻先生写的序文,刘兆吉终于明白了,原来老师发火并不是针对自己,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贰
刘兆吉(1913—2001),中国著名的现代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中国美育心理学创始人,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教育系主任。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他有幸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还要从抗日战争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京津之地顿时成为火海战场。为保存中国文化教育精英,国民政府决定将部分高校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至长沙,合并成立长沙临时大学。
三校合并,虽是战时的无奈之举,但三校名师汇集,优势互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文学院为例,就集中了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杨振声、刘文典、胡适、钱钟书、冯友兰、朱光潜、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众多名家大师。对学生来说,能同时得到三校名师的教诲,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刘兆吉虽是学心理学的,但自幼酷爱文学,且对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的学识和为人仰慕已久。因此,长沙临时大学开课时,他就选修了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先生的《宋诗》和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等课。闻先生得知刘兆吉是哲学教育系的学生,却来选修他的课,很是高兴。那时学生少,师生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每次见到刘兆吉,闻先生都亲切地叫他“密斯特刘”。
然而好景不长,战局恶化,上海、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战火逼近长沙。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示意图
当时不少学生因家乡沦陷,失去了经济来源,无钱乘车乘船去昆明。学校就组织200多名经济困难且身体健康的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徒步去昆明。参加步行团,沿途吃住免费,每人还发一套军装、一件黑棉大衣及水壶、雨伞等日用品。刘兆吉家在山东农村,本来经济就很困难,战乱中又与家人完全断了联系,身无分文,遂报名参加了步行团。
令人感动的是,步行团里还有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等11位老师,他们主动放弃了乘车乘船去昆明的机会,自愿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借此机会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了解民间疾苦,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湘黔滇旅行团”中包括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重要教授
当时不少同学听说闻先生也要参加步行团,非常担心他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谁知闻先生说:“国难当头,步行几千里吃点儿苦算不得什么!我少年时受封建家庭束缚,青年时到清华念书,出洋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平、上海、武汉、青岛等大城市教大学,和广大山区农民隔绝了。尤其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国家有难,应认识自己的祖国了!”
当时的湘黔滇山区,不仅位置偏僻、交通闭塞,且贫穷落后、盗匪横行。而西南联大几百名师生硬是在60多天里,横穿湘黔滇三省,从长沙走到了昆明。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次创举”“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赴昆明
叁
步行团出发前,刘兆吉想起了闻先生讲过:“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他想何不趁此步行机会去沿途采集山歌民谣呢?何况这次步行的路线,正是湘、黔、滇地区偏远而闭塞的山区,是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歌谣而又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啊!
刘兆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师。闻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对刘兆吉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啊!”
谁知真正开始采风,才发现困难重重。因为要采集山歌民谣,刘兆吉常常要离开大队伍,独自一人深入到村寨和田间地头。在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山区,这是很危险的事。他一口北方话,当地人听不太懂,且他身穿出发时学校发的黄布军装,常引起当地人的疑惧。有时,他看到几个山民在田间地头休息聊天,就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但那些人一见他过来,全站起来跑了,弄得他哭笑不得。
当然,也有不少山民得知这个大学生是专门来采集山歌民谣的,即惊讶又高兴:惊讶的是竟然有外地的文化人专门到穷乡僻壤来采集歌谣;高兴的是有人对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歌谣感兴趣。于是很爽快地将自己知道的歌谣吟诵给刘兆吉听。

刘兆吉
采百花成蜜,汇涓流成海。就这样,在68天的行程中,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歌谣。他常把采集到的内容中有些奇特或他特别欣赏的歌谣拿给闻先生看,向他请教。闻一多总是很热情地与他谈论诗歌。那种情景,父亲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1年,已是88岁高龄的刘兆吉还能清楚地记起当年闻先生和他在途中讨论歌谣的情景:
在两个多月、三千五百里路程中,我尽量争取机会向他请教。晚上在沿途山村农舍临时住宿地,与他讨论搜集的民歌。闻先生和学生们同样席地而坐,在菜油灯下,他忘了一天走80多里山路的劳累,高兴地审阅我搜集到的民歌。有时捋须大笑,赞不绝口。老师的期望和鼓励,使我干劲更大。
特别要指出的是,也是在闻一多先生的提议下,父亲才鼓起勇气将《西南采风录》交给出版社出版的。记得闻一多先生看了汇编的歌谣后说:“这些民歌不但在民间文学方面有欣赏和研究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也很有参考的价值。要编辑成书出版呀!不然就辜负了这些宝贵的材料。”
闻先生也很赞赏刘兆吉不怕困难、坚持沿途采集山歌民谣的毅力。在《西南采风录》的序中,闻先生写道:
正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
当时闻先生已是全国知名的教授、诗人了,而刘兆吉不过是个正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闻先生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耐心指导学生采风,又热心为《西南采风录》写序,甚至在序中夸赞这个学生的“毅力实在令人惊佩”,不遗余力地鼓励、提携青年人。

闻一多写的《西南采风录》序言手稿
刘兆吉回忆说:“闻先生主动指导我编选我采集的民间歌谣,并定名为《西南采风录》。在整理过程中,闻先生不厌其烦地以他渊博的语言学、音韵学知识,解决了许多疑难。”而闻先生却在序中说2000多首歌谣“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说自己仅是“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闻先生高贵、谦虚的品格,尽显无遗。
由于当时处于国难时期,《西南采风录》一直拖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刘兆吉已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他拿到刚出版的新书时,多想第一时间把这一好消息告诉闻先生啊!然而就在几个月前,闻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刘兆吉悲痛不已,他回忆说:
当我拿到新出版的《西南采风录》时,片刻的喜悦,就被刺心的悲痛压抑了。因为闻师就在此书出版的4个月前(1946年7月15日)壮烈牺牲了。这是凝结着一多师心血的书呀!我捧着新书哭了!泪花中映着闻师迈着大步跨越在云、贵高原山路上的身影和上课谈话时的音容笑貌。但已听不到他关心的这本书出版的喜讯了。
悲痛之余,父亲决定将这部书的稿费全部献给闻师母。他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达了这一愿望。不久他收到了朱先生的回信。朱先生说,闻先生去世后,梅贻琦校长等人很关心闻师母及其子女的生活,已安排闻师母到图书馆工作,一家人生活还可维持。又说我父亲是有3个孩子的5口之家,一个中学教员,经济上也不宽裕,劝父亲不必寄钱了,但会把我父亲的善意转告闻师母。
肆
闻一多先生在序文中,特别从《西南采风录》中摘出了6首歌谣,其中包括了他和刘兆吉发生争论的那几首: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腰驼。(安南)
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
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
哪一个都市人,有这样的气魄、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
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
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
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
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
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盘县)
闻一多先生摘录出的几首歌谣,从字面来看显得十分粗犷、豪放,也确如刘兆吉最初的认识,“原始、野蛮,似乎是在歌颂土匪强盗”。然而闻先生却透过这些字面看到了更深层的内涵,体察到了更重要的精神,因而他要把这“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伍
闻先生特别强调的“当前这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时期?
闻一多写此序文的时间是1939年3月5日,而就在两个多月前,即1938年12月1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带着他的老婆陈璧君及周佛海等人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的丑恶行为,引起全国上下的强烈谴责。1939年1月2日,即这一年元旦的第二天,西南联大1000多名学生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汪精卫一伙的行径,要求对汪精卫“迅予通缉”,并“处以极刑,以彰国法,而安民心”。
实际上,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就一直存在坚持抗战和妥协求和两种声音。不仅在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甚至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都蔓延着一种悲观情绪。而在“七七事变后,对日妥协的论调并没有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而中止”。一些人认为面对经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战争。
这种悲观情绪,在抗战之初,也蔓延到了长沙临时大学。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所说,在长沙临时大学,教授们每天晚上都要聚集一屋,“谈论着战事”,“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争如何结局的问题”。
但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这些人的败北情绪也在不断发酵、膨胀。据原西南联大教授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写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披露,西南联大文学院在云南蒙自时期,文学院的教授们对抗战前途也出现分歧,甚至在饭桌上也展开了辩论。吴学昭写道:
联大同仁对民族国家出路,战局发展前途,希望虽同,看法不一。哥胪士洋行楼上(笔者按:西南联大文学院教师所住之地),亦不例外。……饭桌上,散步中,谈论的两种不同观点。笼统而言,甲方重感情,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士气较武器重要,无论如何,不可讲和,必须作战到底,“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乙方……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观点不同,论断各异。
陆
闻一多先生是抗战必胜派、乐观派。随着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和败北主义论调甚嚣尘上,闻一多先生忍无可忍了,积压在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趁着给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写序的机会,向那些散布悲观论调的败北主义者们发出了怒吼。
闻一多先生在这段序文里,首先正面回答了刘兆吉认为那几首歌“原始”“野蛮”的看法,认为“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因为闻一多先生透过那几首歌谣,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不是个“精神上的‘天阉’的民族”,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是有血性、有骨气的民族,是完全可以豁出去“反噬他一口”,是可以“困兽犹斗”,是可以与日本帝国主义拼死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正如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所说:“联想到至今还弥漫着的对日妥协空气,他心情不能平静,似乎从这集子(笔者按:指《西南采风录》)体会到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对闻一多先生来说,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自信,而他的自信,也有从这些看似“原始”“野蛮”的山歌民谣中得到的极大启示。他在序文中写道: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在这里,闻一多先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被这些歌谣里蕴涵的乐观、自信、坚强、拼搏、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使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更足了,对抗战前途更乐观了。
有学者如此评价闻一多为《西南采风录》写的序:“闻一多对民歌中表现出的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他看到人民中间蕴藏着力量,从历史上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互相印证,他就觉得有信心。”
《西南采风录》中这些来自大西南边远山区、看似“原始”“野蛮”的山歌民谣,竟使闻一多先生的心灵受到了如此大的震撼,使他听到了人民的心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促使他“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闻一多先生的高瞻远瞩、博大胸怀和爱国精神在他写的《西南采风录》序文中充分表现出来。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