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鲁迅本无师友关系,但有些人用陈、鲁早年在日本的接触说事,1949年后陈寅恪从不透露他与鲁迅的早年交往,遂使陈、鲁关系成为一个话题。
按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陈寅恪的母舅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兼送陆师学堂毕业生22名、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生6名到日本留学。陈寅恪长兄衡恪以文案身份携十二岁的老弟寅恪随行。二月十五日(阳历3月24号)从南京乘日本轮船大贞丸号前往日本,二月二十五(阳历4月4号)抵达日本横滨,行程十天。寅恪在船上与比他大九岁的鲁迅有接触当无疑义。四月初,兄弟俩即随俞明震返回南京。十一月,经俞明震的运作,衡恪终于获得江宁官费留学生名额,再次赴日。寅恪则仍在家塾里读书。因此衡恪、寅恪1902年2月的日本之行,只是利用母舅职务之便,到日本见见世面,为以后留日探路。至1904年,寅恪二兄隆恪考取官费留日,初冬,寅恪跟随二兄同赴日本,在某校跟班进修(关于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陈寅恪本人晚年回忆说是与二兄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学,但亦有人披露寅恪其实是以“亲属滞在”理由赴日,日本外务省的签证时间是半年,并不准延期,故寅恪在当地的小学借读半年即回国),因长兄衡恪与鲁迅同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同学的关系或与鲁迅见过面,但据此认定陈寅恪与鲁迅为“同学故交”则属牵强。关于这一点,如署名散木的文章《陈寅恪与鲁迅有过“密切接触”么》(载《书品》2010年第3期),就质疑几种陈寅恪传记炒作陈、鲁早年关系。
1915年春,陈寅恪在北京曾担任过经界局局长蔡锷三个月左右的秘书,也可能在教育部做过欧文编审(见《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里无陈寅恪薪俸记录,可能在教育部不足一个月),与鲁迅有过短暂交集。鲁迅1915年4月 6日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炭画》一书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由周作人翻译,出版事宜则由鲁迅联系张罗。1914年4月27日,鲁迅收到上海文明书局按出版协议送来的三十册《炭画》后,寄十册给弟周作人,其余二十册分别分赠友人。在寅恪1915年到北京之前,已赠送出十八册。1915年4月6日,这一天鲁迅将仅存的两册《炭画》赠给陈寅恪和齐寿山,也称得上有缘了。
虽然陈寅恪与鲁迅并没有同窗之谊(有鲁迅有同窗之谊的是陈衡恪,但1919年后两人已疏远了),交往也不深。鲁迅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提及陈寅恪,陈寅恪也没有提及鲁迅,但并不代表两人没有一点间接的心气精神上的联系。鲁迅曾经对陈寅恪好友吴宓嬉笑怒骂,对王国维也有批评,却对陈寅恪一直保持沉默。他们本来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一个要全盘西化,激烈地反传统,推行白话文;一个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传承文言文。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擎批判大旗,向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陈寅恪却对此大加肯定:“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见《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页)鲁迅对吴宓主编的《学衡》大张鞑伐,而对陈寅恪在《学衡》上发表过《与妹书》《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一言不发(陈寅恪对吴宓办好这个刊物曾助过一臂之力。陈寅恪支持《学衡》,不仅是因为他与吴宓的个人友情深厚,更主要的是《学衡》的办刊宗旨与他的文化立场基本一致。该刊也确实发表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新旧嬗替时代,承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向海外传播)。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对陈寅恪未有微词。
1949年后,鲁迅研究成为一门跨界于文学、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大学问”。他生前反对过和反对过他的人都争着“谬托知己”,陈寅格当然不会来凑这个热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化学术界掀起“陈寅恪热”,使陈寅恪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和代表。陈寅恪这一形象的弘扬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唤醒了他们的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学术研究领域和知识界、文化界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和“鲁迅”一样泛化为符号象征,与之俱来的是文化学术界的抑鲁扬陈或抑陈扬鲁(刘克敌《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9日)。
1996年,林贤治撰《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对陈寅恪被认定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不无微词,亦有人对林贤治此举不以为然,撰文申说:“针对林贤治此文,我要提出异议。我以为林先生过于执迷文化的新旧之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解过于狭隘,甚至可能从未深读陈寅恪的著作。评陈寅恪‘反背时势’、‘与时代隔绝’,称《柳如是别传》‘狎昵,庸俗,明显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等,隐约有道德批判的意思。不知林先生在此际所悬挂的评判标尺,是否以鲁迅为准星? 若是,则不妨补充一点:知识人的风骨有多种,鲁迅嶙峋,陈寅恪坚韧,实质上却不分高下。”(王涛《旷代的忧伤——鲁迅与陈寅恪的风骨》,载《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鲁迅和陈寅格,都在大师之列。鲁迅重在小说创作和杂文,但同时有汉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实绩在。陈寅恪重在史学,但对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也深有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家》的排序是“鲁迅、陈寅恪、胡适”)。“大师”级的人物,不只“大”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而是从几个方面看去,都是一个稀有的大人物。王国维不只有《人间词话》,梁启超不只有《饮冰室诗话》。他们无一不是既有“作”,又有“论”,影响巨大,且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徐中玉《谈谈鲁迅、陈寅恪、茅盾》,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在道德人格上,鲁迅对那些逢迎趋附、奴颜婢膝者予以辛辣嘲讽。陈寅恪对知识分子曲学阿世、插标卖首深恶痛绝。站在这个角度上,说鲁迅和陈寅恪为同道者是有理据的。论者谓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鲁迅的时代,称之为“民族魂”,下半叶是陈寅恪的时代,称之为“学人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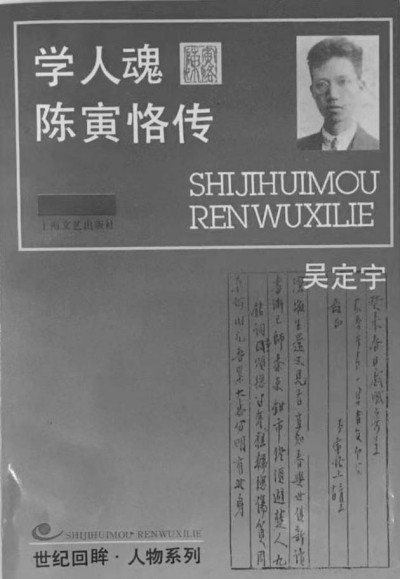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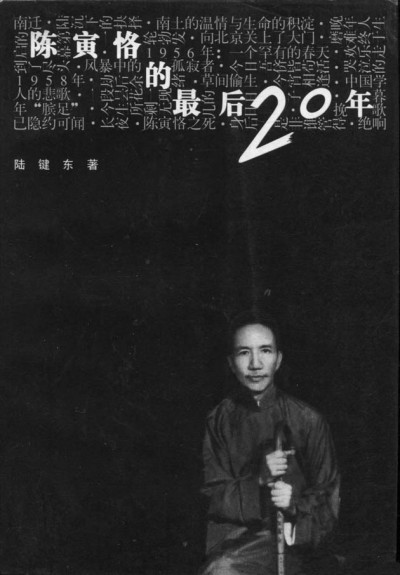
1996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已故吴定宇著《学人魂——陈寅恪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弘扬陈寅恪的读物中,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吴定宇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对引发九十年代中期那一拨“陈寅恪热”功不可没,1996年因此被读书界称为“陈寅恪年”。《学人魂——陈寅恪传》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系统的十大优秀图书之一。作者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再现了陈寅恪在社会动荡不安与文化机制的交替中,如何坚守自己的精神信念,勾勒出陈寅恪的心路历程与命运浮沉,抉示出陈寅恪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最本质的核心价值——学人之魂。至此,鲁、陈双峰并峙,二魂雄杰中华,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