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李诞的一句话红了——“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似乎有种举重若轻力量,透着李诞的“丧”式幽默。
郝景芳在一次演讲里,则说起过这么一句,“在荒谬的人世间,从内心获得意义。”
这句话没有李诞那句讨巧、有传播度、更直接地戳中人群,但却似乎更值得让人思考。
郝景芳,一个关心宇宙、关心人类社会这些宏大命题的科幻作家、学者、创业者,屡屡提及最细腻的人的“内心”。

比如去年九月份在【100Points百人计划】的采访里,她说,“所以我觉得幻想类的文学,最重要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去探讨‘what if’的一个区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通过思考和想象的愉悦感,给我们打开很多出口,在情感上走出现实的一些困局。”她将自己科幻写作最终还是落在了个人的内心情感之上。
比如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采访中,郝景芳谈到了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时的心态,她使用了“平静”这个词。在每次遇到“坎”的时候,她会去非常细微地寻找这种源头的所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达到最后“内心的平静”。
在【100Points百人计划】的这次半程回顾里,我们试图用一些关键词去总结与每一位嘉宾的对话,“心怀宇宙,细嗅蔷薇”最适合用来形容郝景芳——她以极为广阔的视角,最终却落在了最小个体的“内心”世界。从心出发,又回归到心之所在。

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
“我的纠结都是围绕着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做的事情,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因为有这些怀疑和不确定,就会随时对生活很敏感,对于自己的能力也很不确定。”
郝景芳的状态,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她和每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样,迷茫、彷徨、对自己充满了怀疑。
大一那年,郝景芳创作了《生于一九八四》,据说,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来源于郝景芳的困惑,“如果一切都是外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是我自己的,那我还有自由可言吗?”
郝景芳一直保持着强烈地自省。初中时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下,读诗词,谈俄罗斯文学,写周记。那个时候,是她第一次在人生里头发现有“我”这样的存在。从发现“我”,到怀疑“我”,再到之后关心每一个“我”,这或许也是郝景芳在之后关心更宏大的议题时,依然保持对个体的悲悯。
如今的有着多重身份的她,在各种身份之间自若转换。她已经没有了年少的迷茫和自我怀疑,她说,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
“接受自己”的过程里,女儿给了郝景芳很大的影响。她发现女儿在三四个月的时候,对一切开始感兴趣,开始心无旁骛地注视和探索身边的新鲜事物。女儿这种对世界专注的目光,让她意识到人在成长中,一点一点将这种好奇与专注的眼神搞丢。

失去这种纯粹的注视自然带来一系列的焦虑。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提高效率,为了达到目标,为了未来某个还为到来的东西。一切的注视都不是为了注视本身。
李开复在郝景芳2017年11月的新书《人之彼岸》的序言《科幻作家永远是最前卫的思考者》里写到,“景芳的一番话让我深有同感。她说,每一个孩子都天生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有各种奇思妙想,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让郝景芳能够说出“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这样的话的原因,或许就是来自她从孩童身上重新获得的纯粹的注视与纯粹的爱的力量。她从心出发,在焦虑的时代安然自若。

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世界?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郝景芳也感性过。
她去校外蹭讲座,结束后跑去问教授,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外国那样做好垃圾分类?我们明明可以如何如何?
教授说,小姑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垃圾处理吗?没有和她继续纠缠下去。
郝景芳回去后,查了大量国内外的资料,才发现有一群人靠着垃圾为生。她开始重新思索不平等的问题和问题背后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影响着郝景芳之后的专业选择和写作。22岁的她盯着美国收入分配曲线,想着用黑体分布或波尔兹曼分布去拟合,去证明某种普适性。这种联系与思考让她最终决定转入经济系,从经济学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
“不平等”是漫长的历史。郝景芳从高中时转入北京,质问同学关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到二十岁质问教授后发现的垃圾问题背后的不平等,再到转入经济学后研究中发现的王朝经济史里的不平等,她一点点去触碰不平等的根源。
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结束后的一次采访里,记者问她,“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变世界,你觉得是什么事情?”,郝景芳说,“我希望能够瞬间给所有贫困地区的孩子建很好的学校,能够给他们很多的书、很多的图书馆,很多的玩具、很多的资源。”
她这一次没有说模糊的不平等问题,而是用最直白的句子,聊最简单的行为,说出她最朴素的愿望。她知道人类在与不平等的战争里输的体无完肤,但她依然愿意去保留自己初心里对平等世界的追求。

我想追寻的是人群缝隙里的光
郝景芳说她常常不满意在阅读中遇到的那些将人性描写为纯粹是“对生理欲望、物质利益、权力和名声追逐的动物,似乎爱也只是生物繁殖的掩饰”,在百人计划采访中谈到名校、学区房时,她也直言,“我先生是北大毕业的,我是清华毕业的,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孩子不上清华北大无所谓,真的上了清华北大也不过如此。我们是真真正正这么想的。我会觉得其实对于未来时代而言,这些真正长在一个人身上的能力会比一纸学历重要的多。”
她所做的童行计划共享教育,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说她常常想寻找那些被理论所遗漏的东西、人群缝隙中的光,与此同时,她又称为这道光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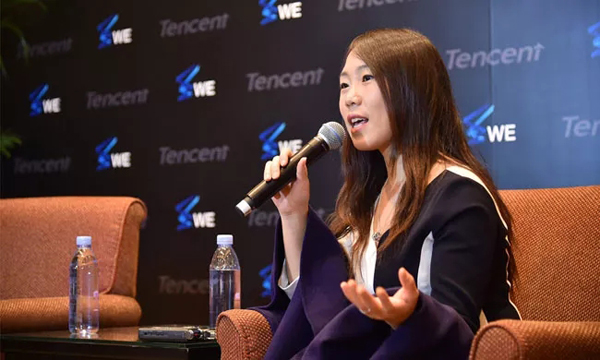
霍金去世那天,她发了一条微博,讲述了在达沃斯论坛上认识的摄影师Platon Antoniou讲述的关于霍金的一则故事:
“Platon去给霍金拍照的时候,霍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眼皮一直睁不开的状态,他的围巾下面全是针眼,每天都需要注射多次针剂,以维持眼睛下面仅有的一小块活跃肌肉活跃。就连这仅有的一小块肌肉,也在慢慢萎缩中。
Platon快要离去的时候,问霍金:“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个词,表明一下您想对这个世界说的话?”
他的护士说:“对不起,摄影师先生,霍金先生已经很累了,他恐怕完成不了了。另外,他眼睛下面的肌肉也在萎缩,最近经常出错,可能他也做不到。”
Platon正在收拾东西想走的时候,突然听见屏幕上光标的声音,他和护士都停下来看,看到霍金靠眼睛下面那一小块肌肉指挥的光标在移动,最后停留在w上面。
护士还是说:“不好意思,霍金先生最近打字经常不受控制,有的时候打出来的字是没意义的。”
Platon正在犹豫,光标又动了。第二次,停留在o上面。过了一会儿,光标又动了。最后停留在w上面。
wow。
霍金对这个世界发出的词是惊叹。
Platon说,这样一个全身都无法行动的人,内心中对于整个宇宙的感觉是惊叹,像孩子一样发出wow。他的心是自由的。”
霍金对这个世界想说的话,就像蹒跚学步时的婴孩,对于世界的一切,都会发出“wow”的惊叹。

以赤子之心从心去出发
如今的郝景芳,不再会去冲动地跑上讲台质问教授“为什么我们不做些什么”,而是用一颗依然温暖而缄默的初心,去做一些事情。她从未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不平等”,也从未放弃对人性之光的追寻,和那一声“wow”的尊敬。
她从来没有阻止自己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她也不止一次试图以独特的风格作为个体存在,于是她不断给予了好奇心,不断重新开始,不断克服这种重新开始背后的可怕;作为一个更加进步更加文明的独立女性,她太知道追逐路上的自由感意味着什么,但她最终也决定了,要保护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坚定,从心去出发。
从心出发,安然自若,感谢与【100Points百人计划】同行的郝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