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3月12日,在“她学术”公益讲座发起一周年之际,清华大学哲学系田薇教授接受了“她学术”公益讲座发起人、田薇教授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李石教授的线上访谈。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多名师生在线参与了访谈活动,以下是访谈实录。(访谈的文字稿包含两位老师在访谈前交流的细节内容,与视频文件稍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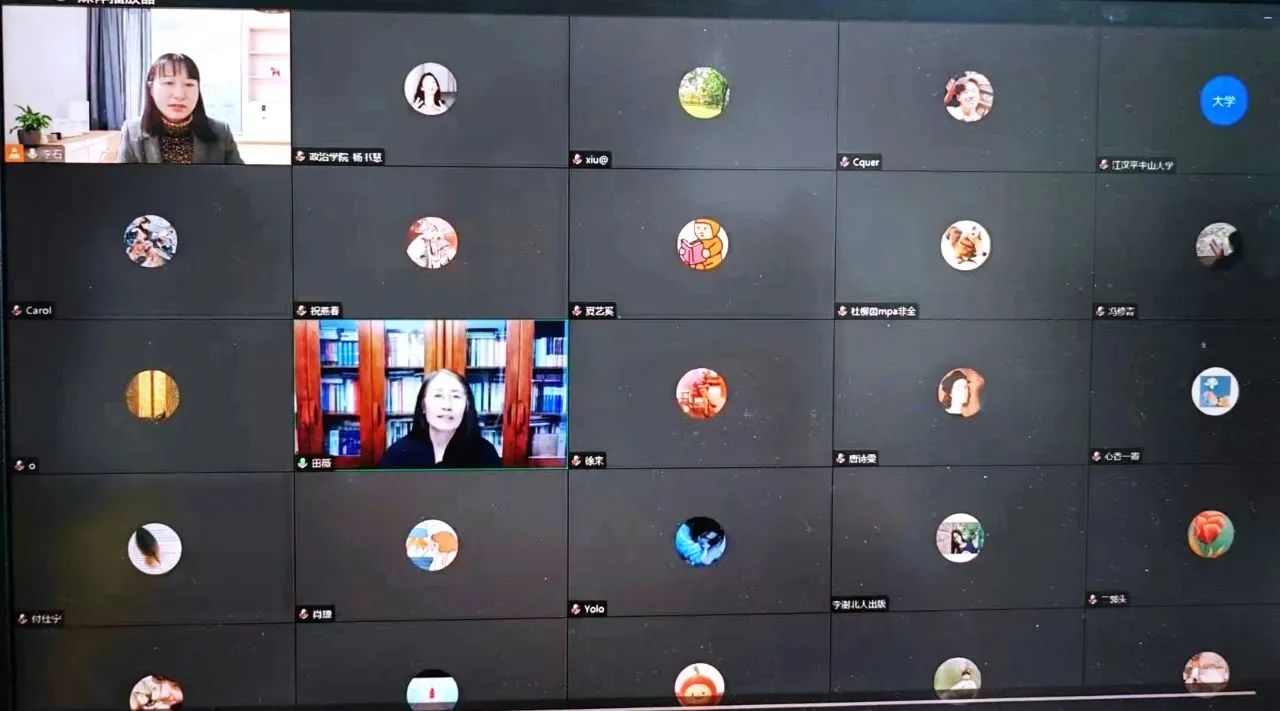
李石教授:田老师好,感谢您接受“她学术”的访谈邀请。您能先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吗?
田薇教授:说来话长。我最初基本上是在一个懵懵懂懂、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情况下,进入哲学的。我是1978年考入人大哲学系。那一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7年是第一年,是各省自行命题考试,1978年是全国统一命题。不过,1977年,我就作为我们公社中学选拔的6名在校生之一,参加了高考。5名考理科,就我一个考文科。结果我和另一名同学上了初选分数线,有了报志愿的资格。报什么呢?当时对大学一窍不通,对于什么专业之类,更是毫无概念。我的一位老师是北京回乡知情,他指导我,报了第一志愿——北大图书馆系。当时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学这个呀?老师说,图书馆系出来的都是给中央首长提供情报的。哦,好吧,那工作多高级呀!结果到了1978年1月份没接到录取通知书,复选落榜了。
这时候,为了迎接1978年的高考,我们县一中恢复成立,我又考到县一中去上学,距离高考还剩下最后四个月,拼命地学习。高考过后,又面临填志愿的问题,哪个哪个大学,什么什么专业,依然是懵懂不清。但我有一个志愿是明确的,就是到北京上大学。由于77年北大录取失败,78年再也不敢失败,因为再失败就要毕业回农村了。所以,第一志愿就谨慎一点报了人大哲学系,接下来几个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哲学系。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对哲学有什么真正的知,仅有的一点和哲学沾边的“知”,就是政治课上的一些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论述。不过我的政治课考分是最高的,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
不过我最初遇到哲学词汇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那是学任何课程,如语文、数学、化学都没有过的感受,就是当我遇到“物质-意识-本原”之类的概念时,它让我产生某种难以进入,像撞到土墙一样的“否定感-拒绝感”。后来想想,可能从反面恰恰证实了,在“哲学和我”之间潜存着某种“内在性-切身性”的关联,只是它在纠缠中还没有被打通。或许,它也是哲学和任何一个个体之间潜在的、需要开启的一种深度的关联?
但无论如何,我在对哲学基本无知的情况下,是稀里糊涂地填报了人大“哲学系”。上了哲学系,还听到北京同学说:人大哲学系天下第一系,当时不知为什么,但感觉挺自豪的。读完了本科,又读研究生。现在回过头去看,感觉自己只有进入研究生阶段,好像才真正开始进入哲学的门。毕业后到清华工作,从此也就和哲学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当初进入哲学的学习之路是懵懂的,那么,在后来的多少年里,我都说,如果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再次选择哲学。因为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以后,我是从心里崇尚哲学的。因为哲学是一个思想的自由的世界,使人超越眼前形而下的经验生活层面,去追索深层的关于世界和人生的形而上的意义,具有非常的思想魅力。
我想,李石你肯定也深有体会,否则,当初不会从化学转到哲学是吧。
李石教授:田老师您说的特别对,我当初为什么从清华化学系转入哲学系,就是因为上了您的马哲课。我当时听您课的感觉就像灵魂被击中了一样,突然发现一个特别深邃迷人的世界。这也侧面说明您的哲学课讲得很精彩。那一定是您自己就非常钟爱这门学术,否则的话,您不可能对学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您身边的人对于您的专业有什么看法?例如您的同学、老师、同事?
田薇教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能切中你提问的意思。比如我的中学同学,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但始终保持着姐妹般情义的同学,她们根本不了解哲学是怎么回事,谈不上对我专业的看法,只要能上大学走出农村,那就是天大的福分。但她们有的是觉得,我搞哲学,不如搞行政,当个官什么的,能给她们的生活帮得上忙。考上了大学的中学同学,95%是学理科的,我们只有3个人是学文科的。想当初,估计大家普遍都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的想法,在刚刚走出文革的时代,哲学不怎么受欢迎。包括我的数学老师,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来北京进修,与我们5位北京上学的同学见面,还说,田薇数学学得很好,应该考理科,可惜考了文科。不过,多年以后,我跟同学们见面,他们对我从事哲学是怀有尊敬的。
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同学,毕业后留在教研领域的很多,搞西方哲学的、中哲的、马哲的、伦理学的、美学的、宗教学的,都有。有时候会在一起开学术会议,有时候会互相参加对方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大家都是做哲学的,对彼此的专业方向有着深度的理解和认同,但做哲学的女同学很少。实际上,我觉得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因为大家既是“同行”,又是同一个单位的教研共同体。我在清华哲学系主要是做西方哲学和宗教学,也做中西比较哲学,一直是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两个分支方向上招收博士生。我和这个共同体中的同事们关系是非常好的,大家在专业上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以至彼此共鸣。同样,哲学系的女老师也是少数,不到五分之一。但每个人都深深地投入哲学,都视之为自己的事业和志业。我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哲学系的。

李石教授:您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和德国哲学,您能谈谈为什么对哲学研究中最“形而上”的部分感兴趣吗?按理说,这部分学问是最思辨也最需要理性反思能力的。
田薇教授:是的,我的确是对哲学形而上学最感兴趣。在我看来,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而之所以对它最有兴趣,可能是因为,首先,作为一个人来讲,我属于那种特别注重精神世界,比较疏离具体实际层面的人,喜欢在思考上追根究底,也喜欢在生存体验上进入某种自由而超越的维度,所以说,在精神气质上属于一个比较倾向形而上的人。其次,从哲学本身来讲,众所周知,德国哲学是最具形而上学思辨性的哲学形态,而我喜欢形而上的思考,也是因为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哲学真正开启了我的思想世界,带给我巨大的哲思魅力。
比如,我们知道,康德将哲学的旨趣概况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 Was kann ich wissen?这是理论理性的兴趣,关注的是,知识是何以可能的。《纯批》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知性为自然立法”。第二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Was soll ich tun? 这是实践理性的兴趣,关注的是,道德是何以可能的。《实践理性批判》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自由即自律,故而“理性为自身立法”。第三个问题 “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 这是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的综合,是人类理性的普遍兴趣和最终目的,《判断力批判》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上帝存在”的公设下,实现德福一致的“至善”。
我们看到,从能够知道什么,到应该做什么,再到可以希望什么,康德由关于自然知识的哲学形而上学,到关于自由道德的哲学形而上学,最后通往关于至善的、并在神圣信念公设下的宗教哲学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康德还将上述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 你从这里可以发现,康德的哲学关切包含着真-善-美-圣、自由和幸福之类的根本问题,如果你对这类问题感兴趣,喜欢追索它们为什么——何以可能,那就必然引向哲学形而上学的求解之路,也必然引向宗教哲学。
说到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哲学和宗教之间实际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性,那就是,它们都在根本上指向“终极关切”,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依靠理性,一个依靠信仰。
李石教授:2022年您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基督教与儒家——宗教性生存伦理的两种范型》,您能介绍一下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吗?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哲学学术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呢?
田薇教授:也不敢说有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吧!但仅就个人的研究兴趣和方向而言,我“主要”是聚焦在“宗教哲学”的视线上。比如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包括关于康德和尼采的,还有出版的一些专著,比如《理性与信仰》、《信念与道德》、《基督教与儒家》、《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都是以“宗教哲学”为主线或主题视域,来贯穿西方哲学、基督教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领域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都属于非常纯粹的理论研究。
主要可以概况为这么几点吧:
第一,我确立和论证了“宗教性”这样一个理论概念。并非我提出的,而是充分吸收和转化了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资源。这个理论概念关系到如何理解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人的存在本性。那什么是宗教性呢?简要地解释就是,无论哪种宗教,从宗教指向的对象上来讲,都是关于终极存在者的观照,像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法、道教的道、儒教的天,都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存在者。我把这种终极性意义称作宗教性;从宗教信仰者自身来讲,各种宗教都是对人性有限性存在的超越性观照,也就是对人性生命的完满性的寻求。如基督教里堕落的人受到罪性的捆绑,要靠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重生和永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完人典型;佛教里众生在生死中轮回,只有通过修行,体悟佛法,才能进入超脱轮回的永恒涅槃境界,“佛陀”就是了悟佛法的典型;道教里也讲凡夫俗子通过修炼真道,羽化登仙,“真人”便是得道成仙的典型;儒教同样主张,每个人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内求功夫,通过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外推活动,实现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圣人”便是这种完美人格的典型。这些都表明,各种不同的宗教追求无不具有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性意义。我把这种超越性意义称作宗教性。合起来讲,所谓宗教性就是宗教存在的终极性和超越性的意义。这种终极而超越的宗教性意义是跳出了各种宗教的具体现象形态,站在哲学形而上学立场上进行透视,从中获取的有关宗教的普遍本质意义。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终极而超越的宗教性何以可能呢?对此,我们借用舍勒的理论来讲就是,它源自人类个体存在本性中的先天形而上学倾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有限性的存在,但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又总是试图超越这种有限性束缚而取向无限性,这种取向正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本性,哲学家称之为“先天形而上学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发现,宗教性属于人的先天的生存结构和精神取向,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宗教性的。所以,我也把宗教性称作形而上学宗教性,它在本质上是“存在的宗教性”。正是基于这种人类存在本性中的形而上学宗教性,才使得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态及其文化传统成为可能,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终极而超越的宗教性生存,也就是信念生存,乃是人类及其个体应对世界和实现自身的特有的生存之道,各种文化传统都是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传统。
第二,正是在宗教性概念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宗教性生存伦理”的思想构架。这一思想突破了学界关于“宗教伦理”的常见。就是说,宗教伦理不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与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科技伦理、环境伦理等并列的某种特殊领域和特殊活动中的伦理,相反,它是人类的整个生存伦理本身。就是说,它既不是以某种善观念为准则的特殊族群的特殊生活样式,也不是停留在行为层面上的某种具有理性普遍性的公共规则伦理,而是植根于存在的宗教性根基,指向人类性-本质性生存结构的本源伦理。我称之为“宗教性、生存性、伦理性”一体同构的存在伦理。所谓生存性指涉人的存在本体,伦理性指涉人的道德经纬,宗教性指涉人的生存限度以及由此关切终极而试图超越的信念取向。这样一来,“宗教性生存伦理”就是具有终极性和超越性根据的伦理存在秩序和源始生存结构,由此打通了宗教伦理和生存伦理的界限。
第三,在宗教性生存伦理的构架下,我对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就是说,将二者作为“共同”的宗教性生存伦理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阐释出各自“不同”的思想特色。我从五个方面展开:基督教的上帝观和儒家的天命观、基督教关于人性的罪性论和儒家的善性论、基督教的圣爱论和儒家的仁爱论、基督教的他力超越论和儒家的自力超越论、基督教的永生观和儒教的不朽观。
这些研究的意义问题实际关涉到我为什么做这些研究,我想讲两点:
第一、最近几十年来,在中西哲学比较中,关于儒家是不是儒教,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在国内学界是一个受到关注又充满争议的前沿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关系到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是不是一种缺少神圣价值和终极支持的世俗伦理文化,关系到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一种没有超验信仰的生活。如果说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族群,那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其内在凝聚力又该如何解释呢?因此,面对这个切身处境中的“议题”,我试图从更深的哲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层次上给出解释,打破世俗伦理和神圣伦理的二分思路,将特定宗教形态转化为普遍宗教性,将特殊宗教伦理转化为本源的宗教性生存伦理。这样一来,在一种新的理论构架之下来重审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个人还是族群,都是宗教性的存在;无论基督教伦理还是儒家伦理都是宗教性生存伦理,只是它们的实现路径和呈现形态不同而已。
第二,从更为深层的学术本身来讲,自从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受到现代解构以来,伦理学的致思理趣不仅偏好概念和命题的逻辑分析路径,而且偏好多元而相对的价值观念,放下了关于整体而普遍的价值形而上学追求,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规范伦理学的层面。可是,缺乏形而上学的支持,规范伦理学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如何突破现代规范伦理学的限度是一个深刻的学术理论问题。我试图沿着康德开辟的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路,进一步推进到宗教形而上学的思路,所以提出了一种关于“宗教性生存伦理”的哲学构想和理论框架。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前面提到的几本书中,而且还体现为半年前提交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是一本25万字的专著,刚刚得到基金委的通知,这项成果获得了“优秀”评级,评审专家们给出了高度评价。总之,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学界同行的充分肯定,还是令人欣慰的。

李石教授: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新作问世。您在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惑或困难是什么?
田薇教授:怎么说呢?我想,哲学的路是一条追根究底-“为什么”的路,这种“为什么”是一种“终极之问”,本身就是最大的困惑和困难,比如存在与非存在、自由与真理、美善与幸福、生死与终极等,都是一些根本性、人类性、普遍性的困惑和难题,我在哲学研究过程中可谓是真切地体认着这些难题和困惑。所以,好像很难更具体地讲我最大的困惑和困难是什么,但可以说一点我在哲学世界里的切身感受。
首先,我对学问有种敬畏感,尤其是对于“存在之问-终极之问”这种哲学形而上学学问-也是神学学问,更是如此。所以行走在这条路上,总有如履薄冰之感。既欣赏和钟爱哲学,专注于其中,也常常感到无形的挑战和压力,挑战自己思维能力的边界,感受那种深度思想的艰难和负重。
其次,作为女性从事哲学,我在哲学世界里的感受,可以用王国维的几句词来描述: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此中人。我们知道,哲学是一种突破经验现实的理性思考活动,昭示的是一种所谓“本然亦应然世界”的真谛和理想。所以,从事哲学,让我一方面体会着深刻的哲思世界的精彩和超越,感觉自己好像比仅仅停留在“现象世界”-经验常识世界的人,多了一双“本体世界”的眼睛-天眼,更加具有透视现象存在和自我存在的理性反思能力,因而也更能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也体会着当下个体自我存在处境的限度和局促。比如,内在的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并不都是和谐一致的,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是当你处在纠缠的心境、跌宕的情感状态时,却需要你沉入哲学理性的深度思考,那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
而且,哲学的表达也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需要非常高强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能力,只是思想随笔,那不是论文,更不是专著,所以哲学写作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我在一本随笔集《思亦诗》里就感慨:要是只写随笔文章,率性情思,飘逸灵动,那该多好!我的一个同事朋友读了《思亦诗》说:“你应该搞文学,不该搞哲学”。
总之,在这方面,作为一种个体性精神人格,我觉得,女性较比男性似乎是不仅情感更丰富跳跃,而且情感与理性纠结为一体,不容易分离,内在张力较大。当然,也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存在体验吧。
李石教授:是的,女性适不适合做哲学,这也是许多人经常提出的疑问。您作为一个女性哲学研究者,您认为女性做哲学有什么“优势”或“劣势”吗?
田薇教授: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优势-劣势”的问题。我不太想说女性的理性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因为搞得好的哲学女性也不少,虽然学界整体上女性属于少数。就像前面说的,由于女性个体精神结构的独特性,可能更会让她感受到某种内在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张力”,因此,承担的东西会更多。不仅如此,若扩展一点考虑,这种精神性结构大概和女性的身体状态也有深层的联系,比如,月经周期、怀孕、生孩子、带孩子,女性身体所有的这些活跃性、变动性、复杂性,不仅使得精神、情感、心灵的层面更加敏感得多,承受得多,而且使得现实的生活层面也要牵缠更多、承受更多。这意味着,做哲学的女性,其实也是任何一个职业女性要做好她的工作,可能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包括对自我的情感调控、对孩子和家庭更多爱和照料的付出。如果纯粹从“工作竞争”的视角来看,那这是女性的“劣势”;但我通常不太从“工作视角”的“优势-劣势”的思路来观照这个问题,更多地是从一种审美生存论的角度去进行女性自身的自我肯定。换句话来说,“自然天命”赋予女性的存在特质是美好的,作为一个女人对这一“天命角色”怀有“自爱和自信”。因此,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应该充分认同和尊重、接纳和保护上天给于女性的这种存在独特性,不应该仅仅从“劳动工具”的意义上理解人,包括女人。这可能从深层次上也牵涉到如何理解性别“平等”问题。
在这方面,我想到,西方女性主义从第一代波伏娃追求平权,要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工作权、选择权、受教育权等等,再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就非常关注和强调女性经验及其自身的独特性,也就是从“正面价值”上肯定自身同男人的“差异”,因此,在伦理学上表现为从正义伦理推进到关怀伦理。“关怀”彰显着同情和理解、宽容和爱的女性经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吉利根就是一个代表,写有《不同的声音》。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地-阴阳-乾坤”互为一体、又各有其位的宇宙观,男女观念也由此引申而来,“女性-母性”往往作为大地厚德载物的博爱象征,所以,我想,女性在自强自立、做一个独立自由人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彰显女性那种爱和包容、接纳和敞开的高超姿态。
李石教授:现在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女学生比例很高,目前我国的本科生中女性比例已经超过男性,硕士生、博士生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女性学者偏少,尤其是优秀的女性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您认为现有学术制度可以如何改进以促进性别平等?
田薇教授:如何从学术制度上促进性别平等,这是一个在制度设计层面上的实践性的操作问题,是一种实现路径问题,这对我是个难题,我最缺乏的就是实践性的设计能力。
不过,如何改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学术制度,首先是如何理解性别平等的意义,在这方面,我可以讲几句。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一个是从普遍人格的意义层次上,无论男女,任何一个个体在人格上,基本人权上都是一样的,平等的,这是超越了具体差别的哲学意义的平等。另一个层次上的“平等”是在这个哲学平等的前提下来讲的,属于第二层次的具体意义的平等,比如各种具体权利,工作权、受教育权、选择权等。但正是在如何“实现”这些具体权利的“路径”上,也就是实践操作方式上,隐含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对此我想到,具体的“平等”可能恰恰要基于“差异”,在充分认同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平等”才是真实的平等,平等才会符合“正义”和“公平”。否则,男女本来就不一样,完全让二者一样,形式上平等了,实质上可能不平等。
前些天我们系博士生预答辩,还说到国外大学如何对待女性升职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的一个女学生刚生完孩子,一边带孩子,一边写博士论文,6月份要毕业,写得非常艰辛。由此引出老师们议论高校职称评审中的性别问题。一个老师说,哈佛大学某系提教授,要求三年必须专门给一个女性名额。另一个老师也说,德国大学也要求给女教授单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专门的应对策略,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李石教授:今天来参加我们线上访谈的女学生和女性研究者也很多,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您对哲学专业的女学生和女性研究者寄予什么样的希望?
田薇教授:四个字概括“亦思亦诗”。一方面哲学肯定是思想之路,这条路的本质是通过概念而进行的理性之“思”;但另一方面,在理性之思的深处是对生命存在的体验和领悟,它是更为本源的精神认知的层面,是灵性之“诗”。在智性和灵性、思想和诗意之间游走,亦思亦诗,我觉得应该是女性人格比较完整和理想的呈现。
李石教授:田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她学术”的线上访谈,您生动的讲述仿佛又让我回到了清华的课堂上。我相信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女学者都从您的分享中得到了许多鼓励。最后,衷心祝愿您在学术上能够取得新的成就,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视频链接:【女性做哲学是什么感受】